著名作家铁凝有一部长篇小说叫《笨花》,笨花即棉花。她曾经说过:“在冀中平原一带,棉花就叫‘花’,而本地的棉花就叫笨花,外地的棉花则被叫做洋花。花和笨的组合,让我觉得是一轻一重,正是日子里不可获取的东西。”冀州作家石振刚的一本长篇小说叫《傲霜花》,也是写的棉花。棉花,经霜愈白,故名傲霜花。
2001年,当时年过古稀的石振刚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20万字的长篇小说《傲霜花》,这在当时衡水文坛引起小小轰动效应,我还在《衡水日报》发了消息予以报道。如今,21年过去了,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作家生活得如何呢?
夏日的一个黄昏,我们几经打听,终于在冀州区湖滨大道东头一个小区里,找到了石振刚老人。贸然敲开家门,一个身材瘦小、有些驼背的老者出来迎接,高兴地拉住我的手,往沙发上让。1929年出生的石振刚,今年已经93岁了,看起来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很足。说起当年出版《傲霜花》,他依然兴奋不已,并给我拿出来几本自己打印出来的大开本《傲霜花》,书里密密麻麻改动了不少。他说,这二十多年间一直在修改这部已出版的小说,力争精益求精,经得起历史的沉淀,并计划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看着老人孩子般单纯的笑容,听着他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为这耄耋老人还能有如此理想而感动和欣慰。
石振刚,1929年出生于冀县东疃村(今属衡水市滨湖新区魏屯镇),1946年考入县立高小,后又转入师范学习。参加工作后,当过干部和理论教员,先后任《河北日报》农村组、《邯郸日报》农村工作部编辑,青年时代就在《河北文艺》《河北日报》等报刊不断发表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1957年回到原籍冀县。1979年平反后,重又舞文弄墨,参与了冀县地名、地方志的编撰工作,退休于原冀州市计划局。
退休后,石振刚决心将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便萌生了创作《傲霜花》的念头。这部长篇小说以衡水农村为背景,描写了一对“农大”毕业的学生石傲和玉枝,1957年满腔热忱地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遭受到反右派运动的打击,之后,经受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但夫妻二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在“劳教”队长、县农林局长以及村大队长的支持和帮助下,仍百折不挠、顽强不屈地坚持了对“傲霜花”的培育和研究,终获成功。我问石振刚老人:“主人公石傲是你自己吗? 你不是农大毕业,怎么懂得棉花育种呢?”他笑笑说:“石傲有我的影子,但不全是。下放时,我曾在冀县粮棉厂工作过,因而对棉花育种很熟悉。”往事如烟,老人的思绪又飘回到历史的长河中……
石振刚对棉花情有独钟,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咏花》:“种在大田里的那些棉花,不仅供广大农民天天观赏,还有着非常大的实用价值,棉花、棉籽、棉籽皮、棉桃皮、棉柴皮等,浑身上下内外都是宝。农村有句话叫,要发家种棉花。在民间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千朵呀,万朵呀,万朵花,都比不上那纯真清丽洁白无瑕的那个棉花;千年呀,万代呀,开不败,岁岁长来月月发,花香香在心里头,花红红遍千万家……”石振刚热爱自己的家乡,当他被政治斗争迫害而心灰意冷时,是家乡的黄土地收留了他,给了他生活的勇气,书中的“滏阳河大桥”“滏西村”“千顷洼”等地方元素便说明了这一点。
石振刚的这部《傲霜花》,写作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完成初稿,然后找过许多人征求意见,这其中就包括他当年在《河北日报》的同事,后来写过《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著名作家浩然,那时浩然住在京东三河县,石振刚登门拜访,老朋友相谈甚欢,也交换了意见。后来,石振刚又带着书稿去过省文联等地征求意见,几易其稿,历时近20年,直到2001年才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石振刚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总编辑缪力对他的支持和鼓励,大拇指伸向他:“好,好样的,够英雄的了! 可惜你的稿子拿来得太晚了,如果你在半年前拿来,那时还有稿费……”石振刚表示,不要稿费,能出版便是对自己最好的肯定了。
走进石振刚老人的书房兼卧室,书架、写字台、床上、椅子、地下都是书和稿纸,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粘贴在书架和墙上的那些小纸条,有些是文字片段,有些是几句灵感,有些是备忘录。跟他同住的儿子说:“母亲在世时,给他整理得井井有条,去年冬天母亲去世了,他的屋子里变得凌乱了,还不让我整理,我也怕给他动了,他找不到地方了。有时,父亲半夜醒了,就爬起来写几句,然后贴到墙上,白天再梳理。”书房的墙上有一幅书法:“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内蒙古老年文摘报社原总编辑孙清池书写送给他的。我忽然想起,2001年出版的《傲霜花》一书的“序”就是孙清池写的。原来,他们俩是同一个村的发小和同学。孙清池曾在“序”中写道:
作者石振刚与我是同村,前后两条街,相隔一方塘。小时候,我们一起蹒跚学步,奠基未来,稍大一点,上树掏鸟,下水摸鱼。抗战时期,家乡流行着一首歌:“碧绿的地,蔚蓝的天,一望千里,这是我的家,冀南大平原……我们就是这样生长在大平原。”白天,我们唱着这首歌在青纱帐里玩游戏;晚上,躺在禾穑上望着朦胧的月色,编织未来。石振刚小时候的名字叫石振纲,老人的心思原本是期望儿子将来立志,振兴纲纪,成为一块补天的料子。但是儿大不由爷,石振刚把“纲”改成了“刚”。本来就够“刚”的石头了,还要使劲去“振”,可见他是一块顽石……
有人说作品是作者的性格,而石振刚的性格在哪里? 恐怕这霜不死、砍不垮的傲霜花性格也就是他典型性格的凝结了。
我问石振刚老人,这些年还写了什么新的著作? 他说,一部纪实文学已经写完了,还在修改,内容暂时保密。老人明显有些耳聋,思维也有些混乱,对我的话答非所问,说话也有些颠三倒四了。石振刚的儿子说,昨天的事可能扭头就忘,而对那些遥远的事情却记得很清楚。尽管这次采访很艰难,没有我预期的那样成功,但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文人的一种执着和气节。老人执意要把我们送到楼下,无论儿子怎么劝都不听。回望站在楼梯口93岁的老人,骨瘦如柴,弓着背,头发霜白,金色的余晖里,如一朵傲霜花灿烂地开放……
作者:杨万宁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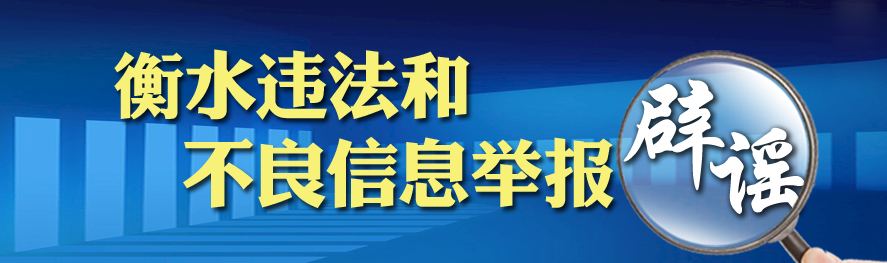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