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时,捧着书本,嗅着淡淡墨香与花香,眼睛扫过一笔一划的方块字,脑海里留下先知们记下的那些未曾熟知的事儿和理儿,心里确实很满足,书自然成了我的“先生”。又恍然想起已故的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生前跟我不止一次说过的“书是古先生”。
如今,一位位忘年交的先生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古先生”。马宝山、史树青、郭纪森、方成、刘金涛、张宗序、张英勤、张天福等,相识于暮年的先生们先后作古,他们的“书事儿”变成了我笔下黄金。
今散记以示纪念他们。
和史先生相识,是我国著名古籍图书发行家郭纪森先生做媒。
郭纪森,是冀州同乡。我读初中时,因喜好搜集地方名人史料,请县方志办的民俗学者常来树老师引荐结识了郭老,并保持通信多年。第一次见郭老是在他返乡探望女儿时,那年我也就十五六岁,他却已是耄耋之年。魁梧的身材丝毫不见弯腰驼背的老态,只是花白寸发和脸上的皱纹彰显着经历的沧桑,浓密的长寿眉下双目炯炯传神,一口冀县话透出丝丝京腔的味道,嗓音浑厚而响亮。
同是十五六岁的年纪,郭纪森已在隆福寺古旧书行当了学徒,三年后出师做伙计,开始了近八十年的贩书、鉴书人生。从勤有堂书铺副经理到创办琉璃厂开通书社自任经理,再到1956“公私合营”并入中国书店,继而退休后返聘一直干到90多岁。凭借着一身过硬的“过眼学”,经手流通的古籍图书难以数计,全国各大图书馆和许多教授的书斋中,几乎都有他提供的文献古籍。他曾从民间抢救出了居我国卷书之冠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书10040卷522函65部。他曾亲口告诉我,郑振铎、冯友兰、洪煨莲、顾颉刚等许多著名学者都委托他寻购过稀世版本。
大学者们向郭老求书,而我作为文史爱好者向他也有一“求”,那就是求证为啥说是“河北人发祥北京琉璃厂”?
众所周知,琉璃厂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特色街区,是明末清初因官员、京外赶考的举人在此逛书市繁盛而起。
1999年夏,尚在上学的我借暑假进京省亲到中国书店拜访了郭老,谈话中他无意的一句,让我兴奋不已:“是河北人奠定了北京琉璃厂的基础,或说是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的琉璃厂,并延续了琉璃厂文化,河北人当中以衡水人为主,衡水人中以咱冀县人为多。”我瞪大眼睛,竟不怎么礼貌地说:“什么?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厂?您再说一遍!”老先生一愣,以为说错了什么话,我忙解释:“这么爆的料儿,您老继续讲讲。”就像小孩听古儿一样,我拖着腮帮子,边听边记。
“由于河北靠近北京,来往比较便利,明万历年间就有衡水人在琉璃厂经营古玩字画和古书店铺。到了清朝科举废除后取代了江西帮而享盛名,亲戚带亲戚、同乡带同乡,我就是这么到的北京,先到隆福寺,后到琉璃厂。”郭老说,这种传承关系,使得不少河北人密集来京以买卖书为生。
当年为了糊口的泥腿子毛孩子们,慢慢从这条街上的贩夫走卒,通过往来于各地的大小书肆,出入于巨贾名流的书斋,逐渐熟悉了书的版本、源流、内容,在搜集整理修复翻印各种古旧书籍中终成大器,成为了响当当的“师”或“家”。
郭老看我听得入迷,又翻箱倒柜找来一本1962年出版的孙殿起(冀县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14岁到琉璃厂)著《琉璃厂小志》送我。书中详载——第三章“书肆变迁记”:上溯道光咸丰年间,下至民国三十五年这一时期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店铺的共三〇五处,而由冀县、衡水、深县、枣强、阜城、景县等衡水籍人士开办的共一百六十四处;第四章“贩书传薪记”:当时琉璃厂以经营古玩字画为主的店铺共一百四十六处,衡水籍开设的有六十处,以书画装裱业为主的店铺共十九处,衡水籍开设的有十一处……
半个世纪后,琉璃厂从业人员中衡水籍人士仍占相当大的比例。郭老给我引荐了版本学家张宗序(深州人,16岁到琉璃厂)和古籍鉴定专家吴希贤(冀州人,16岁到琉璃厂)等。当时他们退休后分别返聘于中国书店和北京市文物局从事古籍版本的鉴定工作。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些成名成家于琉璃厂的衡水籍人士,如碑帖大家马宝山(桃城区人,16岁到琉璃厂)、装裱大家刘金涛(枣强人,12岁到琉璃厂)、一得阁第二代传人张英勤(深州人,十几岁到琉璃厂)等。拜访中,我一一恳求老先生们对郭老首提“河北人发祥北京琉璃厂”的意见,大家纷纷表示赞成,因为他们都是琉璃厂的活资料库。
离京前,张英勤先生还将一得阁墨汁厂几代传人及弟子签名盖章的纪念页赠予我,郭老又送我他手写的《回忆古旧书业概况》《在旧书店学徒期间学习业务的经历》等八方面近万字的影印稿,弥足珍贵。
出于新闻敏感,回到衡水后我撰写一则新闻稿《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通过《燕赵都市报》发出,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都在引用郭纪森的这一学说。
这则稿子,对我今后从事新闻工作起到了一定的鼓励作用,而从城市品牌的角度来看,这是郭老对家乡衡水的一大贡献。尽管稿子发出后,也有不少外地学者对这其中的渊源与衍变有些微词,但的确是衡水人撑起了琉璃厂的繁华,使之薪火传承至今。现在,琉璃厂的槐阴山房、博古斋、金涛斋等20多家老字号仍由衡水人经营着。
从此,衡水、冀州两级政府开始举“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这面文化大旗,举办了“北京琉璃厂——追寻冀人的足迹”文化研讨会、“中国古旧书文化传薪者——琉璃厂之冀州人”座谈会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馆长邹爱莲说:“琉璃厂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早年支撑着琉璃厂的是河北人,他们为琉璃厂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功不可没。”
最后一次见郭老是在2007年春节,那年我已到北京工作。尽管郭老几乎丧失听力,仍坚持用纸和笔与我交流,最后竟拿起毛笔颤颤抖抖写下四个规规矩矩大字“崇德尊学”赠予我。他用这四个字勉励后生,其实这更是他一生做事的原则。在郭老家中,我们谈起刚刚去世的史树青先生,老人有些惋惜。“启功、张岱年、史树青都是我的至交,他们在圈子里被尊为稀有的‘朱砂’,自己只是块‘红土’。常言:‘朱砂’最为珍贵,如今‘朱砂’没了,我们这些‘红土’也倍显价值了!”他说。
郭纪森介绍我认识史树青时,史老也已八秩,还为我的书房题写了斋号“汲艺斋”。而知道他却很早了,古玩圈里会经常说“捡漏儿”这个行话,史老是捡漏儿的国宝级名角。史老说,书读得多,捡漏儿的机会就多,因为学问全部源于读书。六十年一甲子,他访古鉴古未断,曾跟我津津乐道地讲过自己捡的第一个“漏儿”。
“15岁那年,一幅《丘逢甲七绝诗》轴散落在琉璃厂棚子里挂着没人买,我两毛钱拿下。”1953年,他将此物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我就是通过读书知道丘逢甲是台湾的诗人,我感觉人名很重要,研究学问不记人名是不行的。”老人家笑着说,“历史上书画大家和收藏家的名字记得不多,天津一个鉴定家能记一万多人名,我能记五千人吧,郭先生也能。”
史老每次见面总会提读书,为此,我写了篇《国宝史树青:读书养生增学问》刊发在《人民政协报》。他认为,读书是可以健身的,读优美典雅的诗篇,有利于胃病的愈合;读幽默小品之类的书,有助于神经衰弱的医治;读小说能使病人精力集中,有助于康复。
2007年11月7日,史老病逝,享年86岁。不久,“红土”也随“朱砂”而去!2009年4月29日,郭老辞世,享年96岁。
作为文字工作者,我无时无刻离不开书,书中的“古先生”们都是我重要的良师与亲切的益友。我在拙作《文化的力量——与智者对话的思考》中一一追述,今日青灯下再叙一篇献给“先生们”,感谢他们把我带入书的园圃中成长。
(作者刘仝保,系新华社品牌办一部副主任,曾任记者、杂志编辑、主编等)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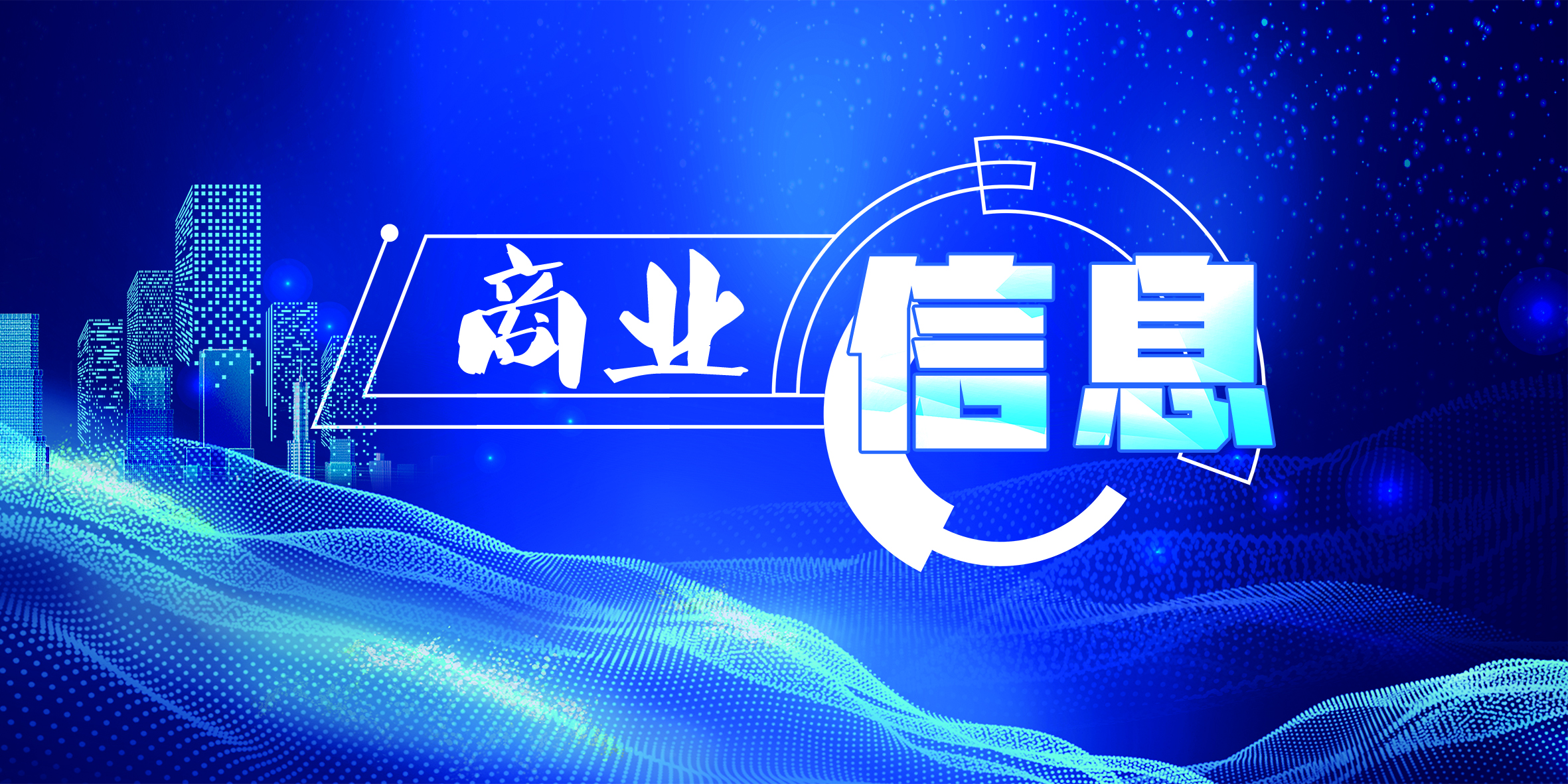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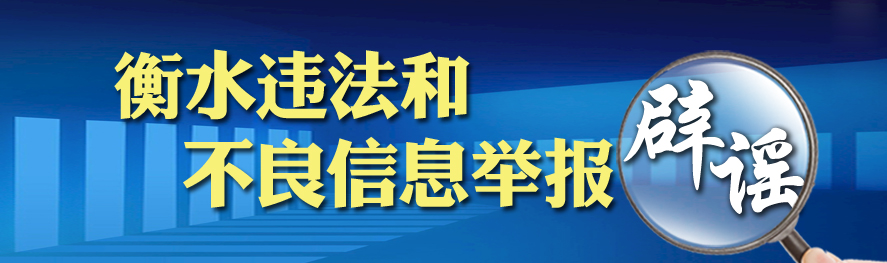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