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弟弟打电话来说,要修老家的房子,屋里的几口大瓮实在没地方放了,问我如何处理。我想了想说,南院的房后不有一大块空地吗,长满了杂草和小树苗,你清理一下,把瓮倒扣在这里吧,估计也没人偷。弟弟高兴地挂了电话,真扔掉这些瓮,他也舍不得。
此后,那七八个大瓮就静静地倒立在屋后,我每次回老家,第一眼就会看到它们,在那里守护着久不住人的家门,无声地闪光。
这些大瓮曾经是母亲的宝贝,是一家人的大物件。父母结婚不久后和奶奶分家另过,两人白手起家盖起三间“金镶玉”北屋,后墙挂了一层蓝砖,前面两个墙角处、门口两边也镶了蓝砖,露出来的正面土坯墙用白石灰刷过。从奶奶家分过来的生活用具只有一口缺了半边的瓮茬,里面只能盛一筲水,那时的母亲只有21岁。她从沟边又捡回一口更小的瓮茬,这口瓮茬只剩下了一尺多高,母亲买来一头小猪,每天都从地里带回一两筐青草和野菜,到年底养起了一头200斤出头的大肥猪,母亲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见母亲养猪得法,身为兽医的父亲从外村借来一头老海膛,说产猪崽时间快,挣钱多,母亲更加辛苦地割草砍菜。那时候,家里的粮食人都不够吃,是没有多少粮食能拿来喂猪的。到了腊月,这头老海膛眼看要产小猪崽了,外面风雪满天,天寒地冻,母亲把西里屋的杂物收拾出来,把老海膛养在屋里,堂屋有做饭的锅头,屋里能暖和一些。几天后,老海膛产下七八头小猪崽,母亲一天熬好几次热猪食,常常顾不上三岁的姐姐和一岁多的我。第二年出了正月,这几头小猪崽毛发光亮,母亲也实在照顾不过来了,父亲就把老海膛还回去,同时送去两只猪崽作为费用,母亲留下一只小猪崽养肥猪。总共才卖了四五头小猪仔,算下来入不敷出,这次养老海膛的经历给母亲带来的阴影持续了好多年,此后家里每年只养一头肥猪。
分田到户后,家里的粮食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前装粮食的两口土瓮和几个瓦罐根本不够用了。父亲找人用石灰抹了两口石灰瓮,又买来两口大瓮,黑色的釉质光亮鉴人,白色的瓮沿,看上去特别大气。父母专门盖了东西两间耳房,一间盛放草料和农具,一间盛放装粮食的大瓮,抹上几个石灰盖子,再不怕鼠咬了,这些粮食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母亲的心里踏实了,她会盘算着把这些粮食吃到来年的收获季节。
此后,父亲又陆续买回几口大瓮、小瓮,除了装粮食外,盛水的瓮也从一口增加到两口,放在院里的枣树底下。东屋西墙下是一口细长的腌咸菜大瓮,耳房里一口半人高的小瓮盛油,饭棚子的墙角是一口面瓮。春天腌咸鸡蛋是膝盖高的小细瓮,等过完麦收,咸鸡蛋吃完,这口小瓮要闲置一段时间,等秋天腌韭菜花再用,一直吃到来年春夏。如果哪天母亲买回一块猪肉,必然会把切菜刀拿到院子里的瓮沿上,正一下反一下地来回杠,然后用手指试试刃口的锋利,才心满意足地切肉去了,那磨刀的声音就是一顿改善生活解馋的前奏曲啊!
奶奶给的那半个瓮茬,母亲多年用它洗衣服,拧过的衣服正好搭在半边的瓮沿上,直到母亲前几年过世,它陪伴了母亲从青春年华直到一生。如今那个瓮茬依然还在,见证着母亲一生的辛劳和一家人一点点努力而来的幸福生活。
作者:刘兰根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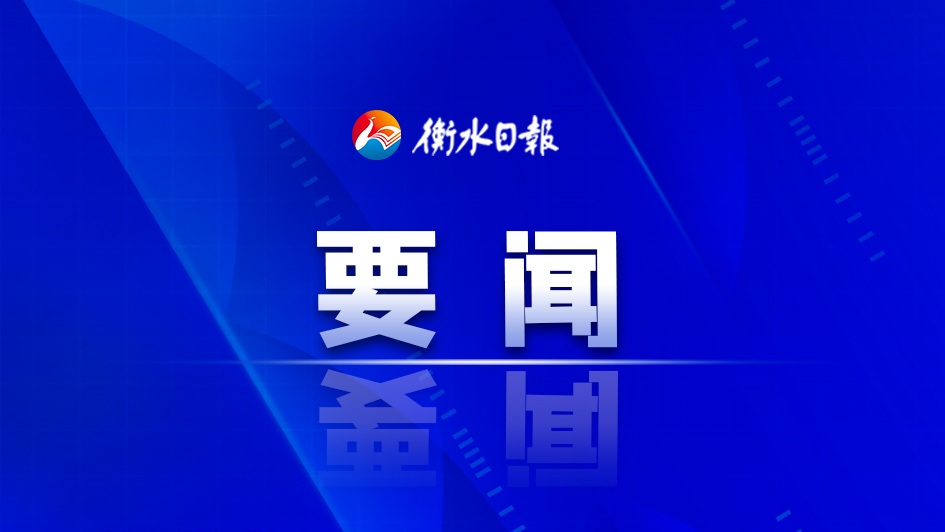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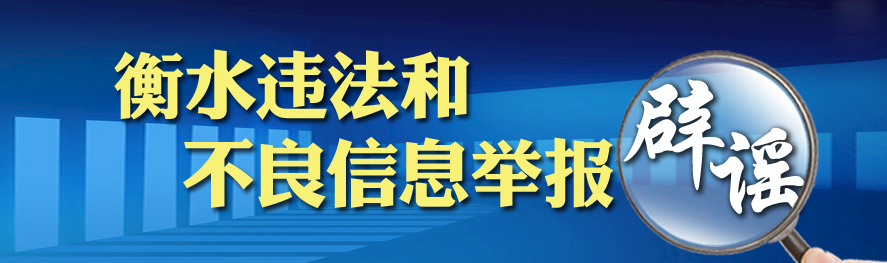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