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烧烤店,都要点一道烤鱼片。意欲寻找一种味道,一种当年在滹沱河边烧烤的况味。
然而,走遍小城野味自居的店铺,总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于是,纠集几个同龄吃货,自备烤箱、木炭和鱼片等食材,驱车回到村庄的老河湾,复制往日的篝火。
流水虽去,河沙依存,故道沧桑,热土含情。缕缕乡烟把我们带回粗犷古朴的岁月。
老河湾位于饶阳姚庄大桥东面的拐弯处。湾内是一片开阔的沙滩,是当年人们“下悬捕鱼”的地方,也是过去曾经吃烤鱼的地点。
河道阔滩的形成,是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县里为防止河流冲刷东岸,组织民工在大齐村西重开了一段河道。虽减轻了河水对东岸的冲刷,但挖出的泥土均积于新旧河道之间,一遇泄洪,新旧河同时进水,分成河岔,两岔间自然形成一块高出河面的枣核型开阔地,成为一道沙化的风景。
人们在河岔的咽喉下网,捕获颇丰。窝棚也常常搭在此处。今生所享的首串烤鱼就在这渔火阑珊的沙岗上。当年那鲜活的鱼片,在“哔剥”燃烧的柴火中浸出点点鱼油,由白而黄,散出淡淡清香。抹一把自制的辣酱,便是天下最美的佳肴。借熊熊燃烧的篝火,再熬一锅新鲜的鱼汤。刚出秋水的打鱼人,就着鱼汤鱼片,干一碗浓酽的老白干,吼几声酣畅淋漓的梆子腔,让人联想到水泊梁山的阮小七。
那时我十来岁,白天和大人一起逮鱼捞虾,晚上不愿回家。听他们讲稀奇古怪的故事。也增长了不少河边的经验。比如,看到水边的土窝窝能很快分辨出哪是小王八的窝,哪是小螃蟹的窝。我们把逮到的王八用绳子拴住腿,倒挂在树上,它的脖子就垂伸得老长。
大人常提醒我们,王八是咬人的,而且咬人不松嘴。遇到这种情况,只管学驴叫,它便立刻把嘴松开。不过,我们一次也没碰到这种情况。
秋后,河里的虾味道最鲜,也最好逮。拉起虾耙子顺着河边走,大虾小虾尽收网底。虾可以生着吃,把虾两头一掰,中间部分就是虾仁,放到嘴里,非常鲜嫩。
看网的老刘头最喜这一口儿。他在网上随手一摸,摘出一只白虾,一掰一挤放到嘴边,眯起眼睛连声赞叹:“真鲜啊!”
我问他:“什么是鲜?”他说:“就是人们常说的腥气。”对此,我虽不敢苟同,却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多年来,总不解“鲜”为何味。偶读汪曾祺的散文《四方食事》,先生写道:“要解释什么是‘鲜’,是很困难的。”他举例说:“我的家乡最能代表鲜味的是虾子”——虾的确是“鲜”,但决不是“腥气”。看来,这“鲜”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们曾捞到一条鳝鱼,黄色有黑线,像一条大长虫(蛇)。由于好奇,便把它用小桶装回家,放到院里的“山东罐子”中喂养。这种鱼在滹沱河很少看到,舍不得吃。
一天早晨,忽然发现罐子倒了,水流了一地,鱼也失踪了。有人猜测让猫尝了“鲜”。
老河湾的味道不仅仅在水里,茫茫沙滩,有的是野味。金蝉刚一出土,就被孩子们收入囊中,即使脱壳高飞,攀上高枝,也难逃玩童的罗网,断其翅,下油锅,酥香可口;林中雀的高补;空中雁的粗放;草中蚂蚱的单纯。以其各自的风味丰富着人们的味蕾。
最过瘾的还是逮兔子。人们使用套、夹、笼、网、猎枪等工具擒获猎物,乐在其中。
沙滩之上,常常听到一声枪响,疾驰如飞的猎犬一路狂奔追捕野兔,直至擒获。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狡黠的野兔善于拐避躲藏,时常凭智慧躲过劫难。
猎手的枪都是那种单筒长杆,木头托子,装黑药铁沙子。这种枪命中率只有五成。一管药出去沙子呈分散状,减弱了弹药的力度和射程。高强的猎手讲究的是悄悄接近目标,近距离射击。这种枪最适合打击成群的家雀。
猎手们下洼打猎时,都是斜挎着一个帆布兜子——猎袋、扎腰带、穿靴子、打腿带。时常独来独往,有时也结伴,但都相隔一段距离,默默地保持进攻的队形。发现目标后不说话,悄悄用手语。或包抄围堵,或打“伏击”。
每个村子都有十个八个的猎手,你看到谁家墙上常钉着兔皮,谁家就是“猎户”。
兔肉天然无邪,随和低调,掺什么肉就随什么味。生活中开玩笑,人们常把那些没有自身立场的主儿称为“兔子肉”,却也形象逼真。
飞禽走兽的滋味令人陶醉,而湾里的野菜更是流传千古的吟唱。马齿苋、拉拉菜、车前草、蒲公英、苣苣菜、扎蓬棵等等,以不同风姿,张扬着个性。
一开春儿,人们手提竹篮,身背柳筐,来到河边。此时的野菜刚出地皮,鲜嫩水灵。用刀子剜下来,用河水洗干净,将筐、竹篮挂在树上或放在船头,等水空干了,才带回家。
这些野菜有的可以生着吃,如苣苣菜、蒲公英,蘸酱裹饽饽,非常新鲜;有的用开水泼一下,如扎蓬棵,剁碎后放上蒜泥或油炸的红辣椒、花椒油,辣乎乎香喷喷脆生生;有的可以用来包饺子、蒸包子,如拉拉菜,让半开的水轻轻一泼(水不能太热,否则会失去天然的辣味),随后立刻用凉水透一下,挤干剁碎以后掺上猪肉馅,包出的饺子很是讲究;有的菜可以凉干以后吃。此吃法应首推马齿苋。夏天釆那些肥嫩的晾干,冬天吃时先用水泡开,然后用手一抟,挤去水分,剁碎,掺熟猪肉馅(五花肉)、碎粉条,包饺子或蒸包子,最好就热吃,味窜。
还有的东西可以随摘随吃。如野葡萄、嫩呆瓜、红榴榴及茅草的花苞,放到嘴里咀嚼吮吸,令人爽透了身心。
这是老河湾的馈赠,它带着滹沱河的脉脉温情,带着天然与纯真,让人们口齿留香,充满生机与激情。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釆蘩祈祈”。如果说《诗经·小雅》中釆蒿人走出城郭宫廷,是在追寻田野的风雅故事,那么现代人们在河边的寻觅就是一种对远古生活的回味。只是来得更真实,更热烈,更有底色。
从生物学角度看,人处于生物链的最高端,当然有些随性。但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现在很少有人在滥杀无辜,由对自然界的硬性索取上升到尊重自然、认识自然、保护自然。懂得了与之和谐相处,共存共生。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我想,若长此以往,大自然对我们的回馈绝不单单是一道烤鱼片和兔子肉。
作者:刘善民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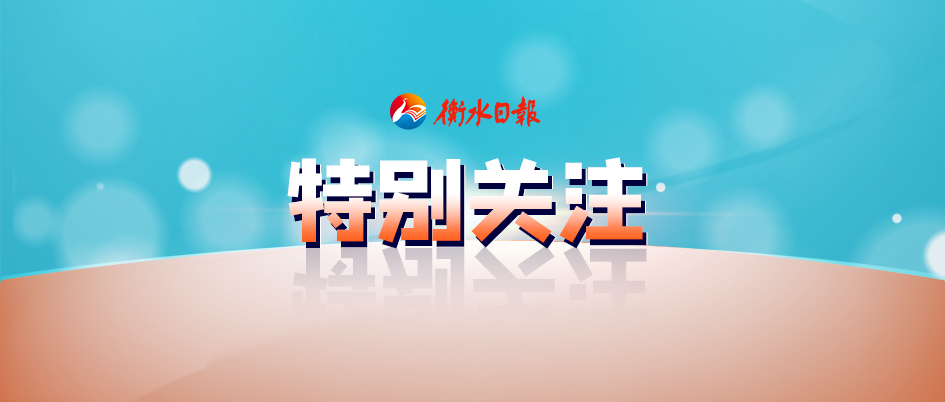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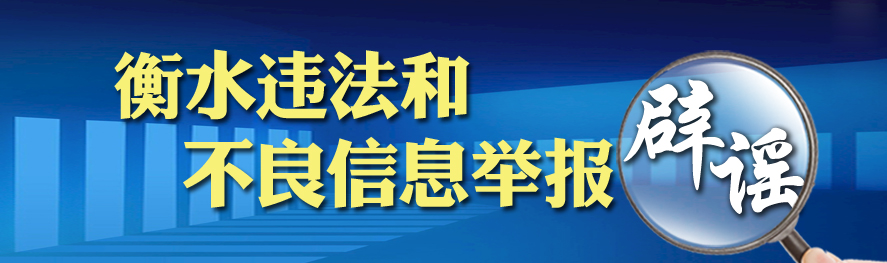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