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从早到晚,下了一天一夜,又一天一夜。
黎明,我躺在床上,听楼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持续而有节奏。
雨点落在花树的枝叶上,唰唰唰的,像悄悄话;摔在地上的,噗噗的,声若叹息;砸在停放的车顶子上,敲敲打打,有催人上路的感觉;一阵风,挟了满把雨丝,呼地甩在窗户上,玻璃啪啪直响,可是意欲摇醒梦中的人?
自然界的风风雨雨,连着人的感情。比如现在,一阵风雨把我从床上刮起来,坐在床沿看天气,想事情。
九月的雨,和春夏的雨不同。春雨贵如油,太珍贵了,不好求;夏雨有时来得疯狂、急切,像一些人的脾气,任性;九月秋正浓,雨不大,也不小,缠缠绵绵,是有情的。
那一年我结婚,老天爷就送来一场九月雨。
1985年9月在沧州当兵。即将退役,突然想在部队期间把婚结了。考虑到部队整训执勤都很紧张,故没有惊动战友们,也不想让家里为我的婚事大折腾,简单低调地举行个仪式就得。于是,请了5天“事假”,买了张汽车票就回家了。母亲说:“你连来带去5天,家里也没准备,让人怎么办?”
父母都是好脾气,不管怎么说,事还得办。但天气不饶人,雨整整下了七天七夜。
新婚之夜,房漏得没有一席干巴地儿,母亲噙着泪说:“你们去老屋吧,老屋的房顶积了坯,不会漏。”
果然,老屋没漏。三间房,我们睡东间,弟弟和老嘎(刘玉庆)睡西间。他俩刚从北关村回来,去送盛豆腐脑的大瓮,是为我们搞服务的。顺便说一下,老嘎不在了,他住院其间,我没有去探望。真的不知道……这是我一生最自责的一件事。
第二天,我要赶回部队。这是纪律,一天也不能耽搁。
我村离县城八里地,道路泥泞,须步行。我们赤着脚,提着鞋,相互搀扶,虽艰难,一路上不时自嘲,说说笑笑,倒有几分浪漫。路上,还碰上了两个骑高头大马的人,他们去县城买塑料布,用于盖房顶(那时农村都是土房顶)。听说家家户户漏房,县城的塑料布被卖空了。
走到河边,看到平日干涸的滹沱河积存了不少水。还上演了一场“老猪背媳妇”。她趴在我的背上说:“早知道这么难走,不嫁大齐村。”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媒人曾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就是来我村的半路上被风沙刮回去的,面都没得见。后来,我曾说:“大齐村的老少爷们儿,可要争口气啊!”
当年,从饶阳到沧州市没有直达的汽车,要坐车到河间再转车。而且,每天只有一趟。记得到饶阳车站后没有赶上,我们坐“二蹬”(跑出租的自行车)去肃宁的万里车站,才乘车去的沧州。
到沧州后老连长看出端倪,让我打立正并“如实交待“。只好坦白。连长说:“这就对了,我也干过一回这个事。”连长请我们吃过一次饭。那一年,我才二十四岁,正是需要别人引导的年龄,首长的一个点拨,战友的有意提醒,何等重要啊!心存感激,不敢忘怀。
还有一件事,也是九月,也和雨有关。九月的雨,情深。
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追悼会那一天,举国同悲。学校即大庙,村里有事都集中在这里。先是收听,三唱机的效果不好,但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听得非常认真,不漏掉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追悼会后,有个议程——“老革命”发言,然后吃忆苦饭。
雨唰唰的。没人穿雨衣,哭声连着雨声,一个女同学悲哀过度,栽倒在现场,被抬出了队伍。
我爷爷是“老革命”,村里推举他发言。台上有个电线杆子,杆子一侧有根缆线斜埋在地上,面对全村群众,爷爷有些激动,帽子被线兜了一下,随风飘走了,老人不顾及,拿着稿子念念有词。我发现,他眼角溢满了泪水。
雨淅淅沥沥地下,昨天喝点酒,今天还难受。喝了酒就容易胡思乱想。比如,在窗前听雨,想自己新婚遇雨,回忆伟人陨落后泪奔如雨等等。或云或雾或风,甚至想到雪,虽是云山雾罩,却有滋有味。
忽然想起了蒋捷那首《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洒家一介草民,既无年少的逐笑狂欢,亦无壮年的孤苦伤怀,而今,“鬓已星星也”,不为命悲,不为命喜。感谢生活,感恩时代。以平淡之心,面对自己,面向未来。
天地之间,小雨依然淅沥着……
作者:刘善民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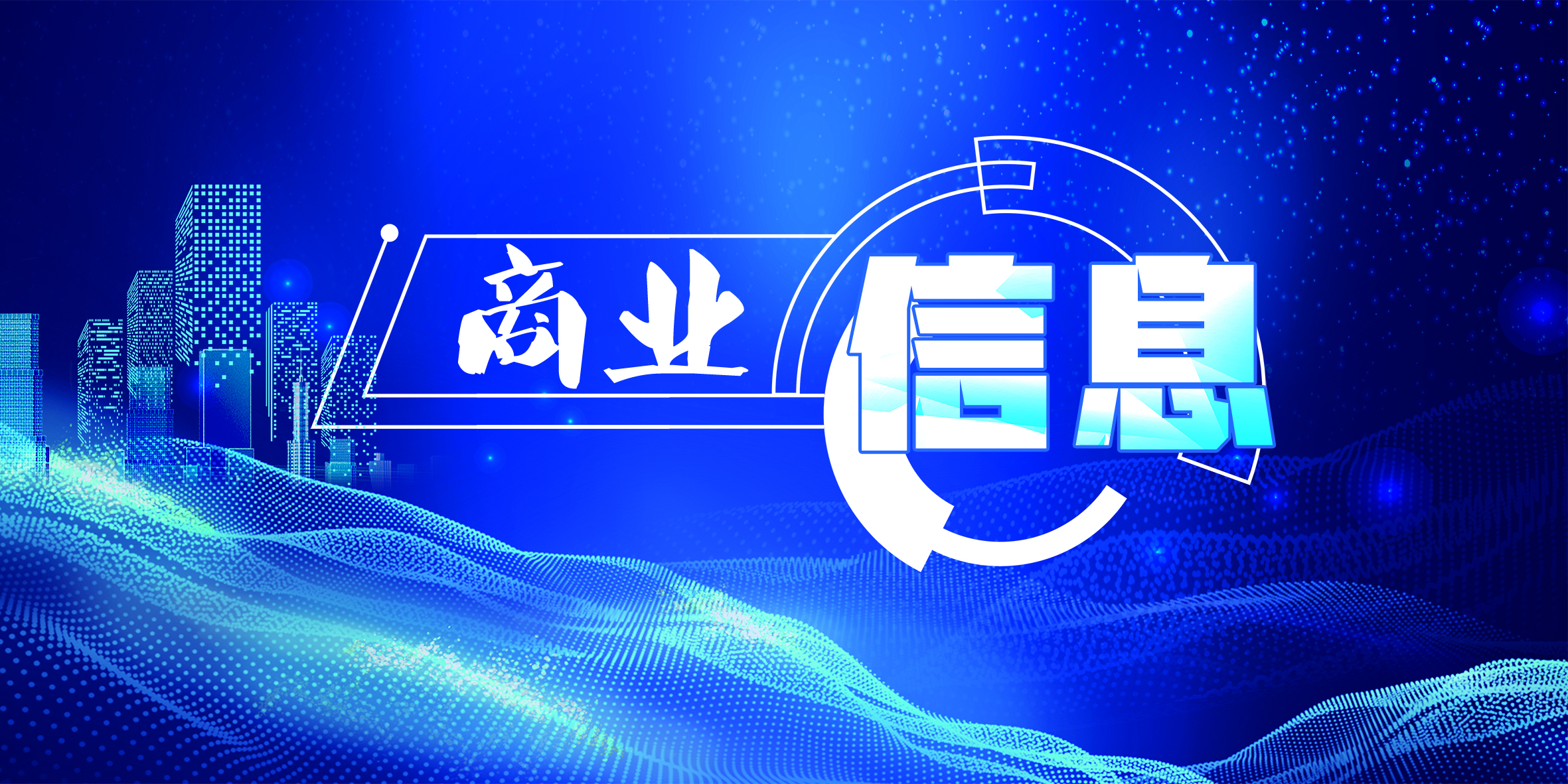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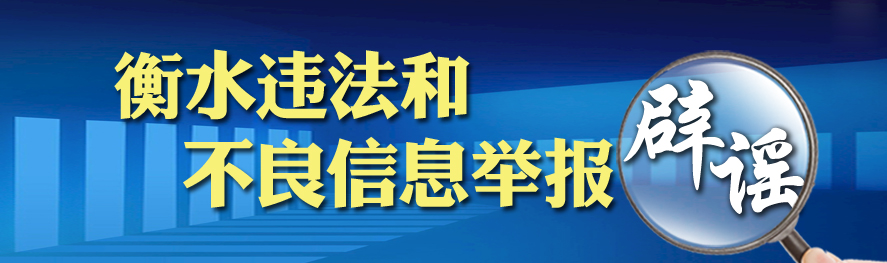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