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依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是在央视综合频道一个经典诗词咏唱的节目里。模样俊俏的小姑娘,来自新疆且末县的大山“那一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缘、阿尔金山的北麓。
且末县的历史悠久,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第一次将且末古国的情况带回内地;唐玄奘自印度取经回来,也曾经过这里,《大唐西域记》里对且末有记载……
依利米努尔朗诵的是作家王家新著名的新诗《在山的那边》。她用动听的童声,诠释了一个耽于幻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心少年的美好愿望: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
山那边是什么呢?
妈妈给我说过:海。
哦,山那边是海吗?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
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
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
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
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
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
妈妈,那个海呢?”
主持人好奇地询问依利米努尔,你为什么自称“小红柳”呢?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红柳树能在极度干旱、没有水的沙漠里生长,生命力很强,所以在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小红柳’”。小姑娘还说,她之所以能从且末走到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走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是因为有一个好老师李桂枝的培养支持。李老师2000年从河北保定师范毕业,来且末支教,就像一株红柳树一样,扎根在这塔克拉玛干沙漠了……
“小红柳”挥了一下拳头:我这次虽然没有能“晋级”,但我会继续努力的,就像《在山的那边》的诗里讲的:
“在山的那边,是海!
是用信念凝成的海……”
“小红柳”的故事让我感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并且它还引发起我对寻找红柳树的深刻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从报纸上看到关于红柳树的报道,知道它是一种不寻常的树,是沙漠和高原上最美的树。于是对红柳产生了一种崇拜、热爱的冲动,盼望有一天能亲眼看一看、摸一摸这“伟大”的红柳树。
第一次机会出现在2003年夏天。那次虽然到了新疆石河子、吐鲁番,但没有寻找到红柳。听当地人讲,塔里木盆地周边的沙漠地到处都有红柳树。由于任务紧急,只好怏怏而归。人常说,愈是找不到、看不到的东西,就愈想找到它、看到它。我从资料上了解到:红柳树,又名桑树柳,是一种灌木,最高能长到两米多。它的茎秆为枣红色,墨绿色的叶子非常瘦小,属于鳞片叶,一般在春夏之交开花,花为粉红色。它能在高原、盐碱地、戈壁荒滩等贫瘠的土壤里生长,能顶风冒雪、防风固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2007年9月,我有幸再次赴新疆出差,这次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据当地人说,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9月21日上午,我们从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喀什出发,去地处沙漠边缘的岳普湖县,在路经疏勒县时遇到大片红柳树。我“强烈”要求司机在路边停车。
难道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绚烂、红艳、茂盛、如熊熊燃烧的烈火般的红柳树吗?”其实,它就像家乡根治海河前盐碱洼地里的灌木“红荆”一般,一人多高,开着粉红色的花。只不过红柳的茎秆韧性更强,细的可以用来编筐,粗的可以当筐框,还可做农民平整土地的耙子……
回到乌鲁木齐,曾在中央党校一起学习的同学刘刚来看望。我兴奋地向他报告:“在疏勒和岳普湖县我看到红柳了!”没想到他哈哈大笑,那笑声中似乎有一种“少见多怪”的意思,让我有些不解。细谈起来,才了解到,原来他祖籍安徽,父亲随一野部队进疆,离休前曾任新疆建设兵团副政委。刘刚是建设兵团的第二代,1951年出生在乌鲁木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亲自经历了建设兵团建设“两圈一线”的战天斗地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
所谓“两圈”,是指围绕塔里木盆地和准格尔盆地靠近沙漠的两个“大圈”周边,大力种植能够在戈壁荒漠残酷环境生长、并能防风固沙的红柳。而“一线”则指的是守卫边疆、建设边疆、扎根边境。刘刚还说,我去的疏勒县和岳普湖县,是建设兵团的农三师的驻防地,是当年他们种植红柳的地方。红柳虽没有松柏的伟岸,但它以特有的能忍耐、能吃苦、能抗争、能奉献的品格,在戈壁荒漠中顽强地成长,像军垦战士一样守护着祖国的边疆。
一席话说得我茅塞顿开。望着刘刚黑黝黝的面孔,我不由得肃然起敬:红色是最美的颜色,红柳是最神圣的树。而刘刚不也是一株红柳吗?只不过这当年的“小红柳”,随着岁月的消磨和生活的跋涉磨炼成了“老红柳”——一名德才兼备的兵团中层干部了!
作者:张锡杰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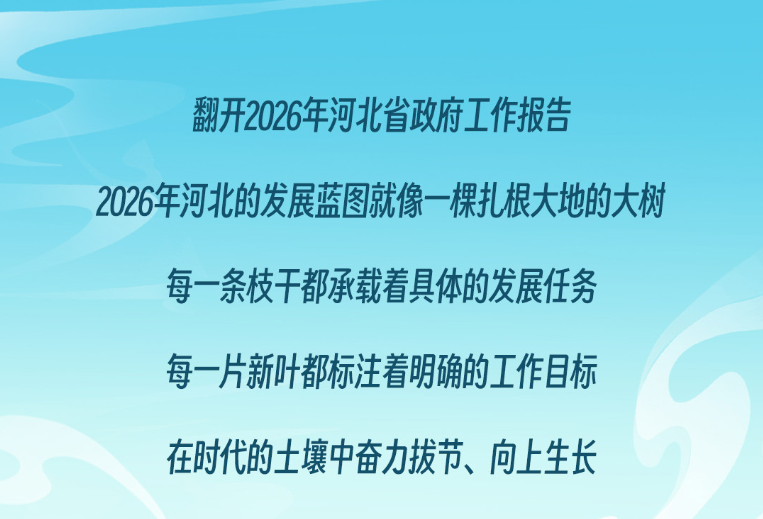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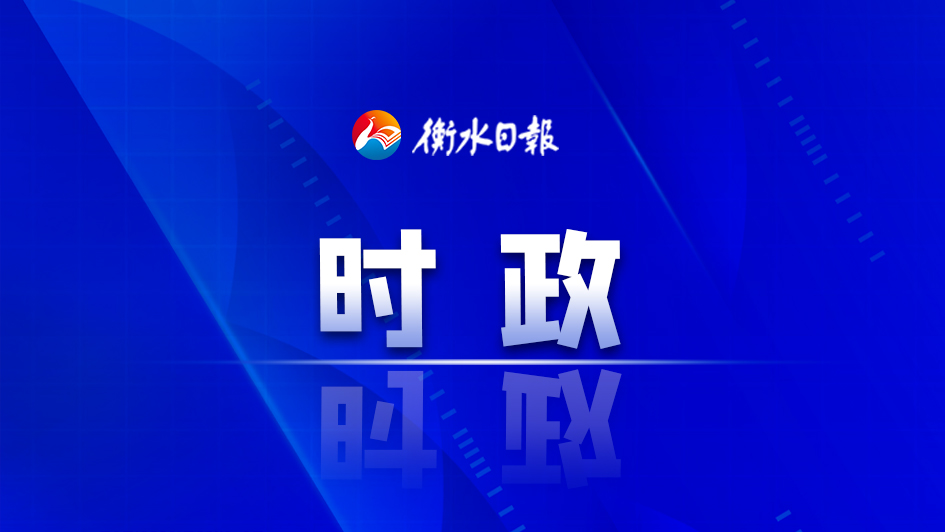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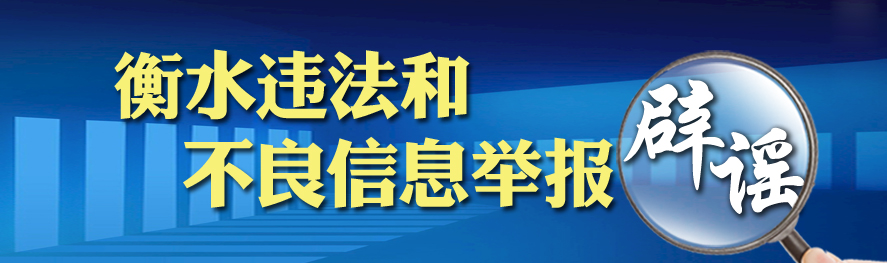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