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川董子园
董仲舒对汉代社会制度设计的贡献
汉初七十年,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社会制度设计方面建树不多,基本上因袭秦朝制度,只是法律制度有所改观而已,因此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孕育着社会危机。武帝登基以后,直面当时的社会问题,广泛听取意见,逐步解决问题,从而使国家的各类管理制度日益完善和优化。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的意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概括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的论述,择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春秋公羊传》的核心思想是“大一统”,董仲舒以经治国,极力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势力。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国家一统、中央集权上升到天地之道的高度,促使汉武帝下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封土过大、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图谋不轨的社会顽疾。更为可贵的是,“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朝野上下高度认同,《春秋公羊传》的学术思想从此成为国家的主流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有了“久分必合”的独特历史景象。汉代以后,无论出现什么分裂现象,即使是北方游牧部族入主中原,掌握了全国政权,也都要奉行大一统的观念,坚持国家统一和“道统”传承。这种情形与欧洲历史上的蛮族入侵,打断历史传承,分裂为多个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与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中断文明消失更是大为不同。元代、清朝都不是汉族政权,但他们都坚持国家大一统,在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与汉族政权大致无异。近代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从朝廷抵抗到民间的遍地反洋烽火,都体现了国家一统的精神力量。其二,大一统的文化体制。秦朝实行文化专制,“以吏为师”,设“腹非之罪”,不允许朝廷法令以外的任何学说流传于社会,董仲舒说秦朝是“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汉代初年,除携书令,各家学说逐渐复苏。但是朝廷提倡黄老之学,儒学虽立为朝廷博士,但并未真正受到重视,基本属于民间学说。这种情况反映到朝廷的国家治理方略,就表现为“无为而治”,中央政权弱化,对内统治无力,对外屡受匈奴劫掠。董仲舒认为这些情况的根源在于,师异道,人异说,教化不统一,政令当然就不会统一。所以汉初七十年间,几次制礼作乐均因争论不休而放弃,对匈奴的方略也是游移不定。所谓“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更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设太学,立儒学五经七博士,在全社会倡导儒学,在郡县设庠和序(即不同级别的学校)实行儒学教育。从此,儒学由民间学问上升为国家学说,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化。其他各派学说并未因此而灭绝,而是在民间继续发展,因为董仲舒的建议是“勿使并进”,这就形成了儒学为主体其他各派在民间流传的局面,这种格局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才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元、清三朝,统治集团均是北方游牧民族,但他们都没有用其本民族的文化作为国家主流文化,而是坚持儒学治国,虽然有所损益,但基本格局未变。最为突出的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北魏政权建立初期,实行鲜卑族原有文化和统治方式,在冯太后谋划和支持下,孝文帝顶住压力决心汉化,读儒学经典,行儒家礼制,使得险些中断的儒学文化传统得以接续。元朝在崖山之战灭亡了南宋政权,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华”,其实大谬,中国传统文化在元朝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有所强化,如书院的发展,在元朝得到朝廷重视,官府给予资助,形成了书院的发展期。清代满族风俗有一些体现在了统治方略中,但清朝的文化主体和治理方式均与汉族朝廷无异。这种历史现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其他三个均已湮灭,惟独中华文明不仅未曾中断,反而愈益丰厚,影响广远,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大一统”,依然是师异道,人异说,没有主流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序延绵不绝将不会保持,如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也会中断湮灭,也就不会有东亚文化圈和对世界的广泛影响。其三,官吏培养、选拔和任用制度,即早期的文官制度。西汉初期,官吏来源基本有四类情况,高官子弟、战功受奖、年久积累、捐资买官。这样的官吏资源短期内尚可维持,但长久以往必见大弊。
因此,董仲舒提出三点建议,在朝廷设太学,地方设庠和序,广泛培养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吏人才;责令地方官每年举荐两名德才兼备的人才给朝廷;朝廷对这些人才详细考察,“量才而授官”这是一套完整的文官制度,历史上称作“察举制度”,到隋朝发展为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先进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极力推崇中国的文官制度,英国设计文官制度时,系统借鉴了科举制度。因此西方教科书认为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其四,限制官吏与民争利。董仲舒认为,官吏的任务是教化万民治理社会,因此朝廷发给俸禄,百姓的任务是兴产置业“皇皇而求利”,因此官吏在得到俸禄的同时不能“置产业”与民争利。他说“天不重与”,上天生万物,但是有角的动物不能有利爪。董仲舒举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仪休“拔葵出妻”的故事论证不与民争利的道理。他认为“已有大者,不得有小,天数也”,建议“使诸有大俸禄,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他自己身体力行,终生不置产业,被称为“醇儒”。这项管理制度影响深远,当今推行的官员不得经商与董仲舒2000年前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四,“调均”的经济政策。西汉初年,朝廷奉行无为而治,社会经济以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为主,经济政策是放任自由。经过几十年发展,这种自由经济政策的必然走向是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计了“调均”的经济政策。他说,“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董仲舒认为,贫富的标准应该以“中和”思想为指导,无大贫亦无大富则社会安定。其实从古至今,所有社会的病态根源全在于两极分化,富则骄,贫则忧。当年董仲舒阐发的这种社会轨迹在以后不断上演,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李奎良 编辑:贾亚楠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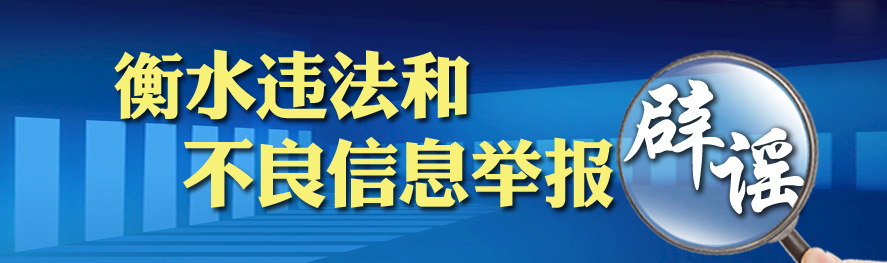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