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柳香漫过饶阳县东里满镇南韩村,77岁的陈铁抓坐在院里的树下,蓝布衫领沾着几缕浅绿柳屑。他膝头摊着半成品簸箕,枯瘦的手指顺着柳条纹路慢慢摩挲——这个带着自然气息的手工器物,曾是全村的致富法宝,如今也藏着这门老手艺的过往与未来。


院角堆着捆扎整齐的柳条,地上摆着各式“老伙计”,都是陈铁抓编簸箕的必需品。“咱村的柳条是自家种的,每年立冬时收割,这时候的柳条柔韧度正好,编出来的簸箕结实耐用。”他指着柳条,话里满是经验,“收割后先刮皮,用去皮刀顺着纹理轻刮,要么削不干净影响美观,要么会损伤柳条影响结实度。刮完得摊在阴凉处晾三四天,晒到摸着不发黏、有韧性就停,晒太干编的时候容易断。”
柴草堆后藏着半露的地窨子口,黑黢黢的洞口透着微凉潮气,这是他专属的“工作室”。“要用时再把晾干的柳条放在水里泡软,地窨子冬暖夏凉,能一直保持柳条的湿度和柔韧性。”陈铁抓从里面拎出一捆柳条,演示起编簸箕的步骤:左手固定几根柳条,右手将另一根按特定纹路穿插,每一次穿插都要用力按压,确保接口紧密。指尖翻飞间,柳条似有了生命,“这不是简单劳作,每根柳条的穿插都得顺着纹路来,就像跟它对话。”
摩挲着膝头的半成品簸箕,陈铁抓的思绪慢慢回到14岁时的秋天。“那时家里条件不好,为了生计,跟着老一辈学编簸箕和笸箩换钱补贴家用。”从选材、去皮到泡水,每一步都要拿捏力度,“学会不难,做精却需要长时间打磨。”后来,这门手艺成了全家的收入来源。农闲时,家家户户都钻进地窨子编簸箕、笸箩,院子里堆着柳条和半成品,空气里飘满柳香。“我一天能编两三个,卖的钱能添不少东西——孩子们的学费、家里的油盐酱醋,全靠这双手。”周边枣强县、故城县的村民专程来买,订单常排到半个月后。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柳编簸箕的需求越来越少,村里掌握柳编技艺的人也逐年减少,年轻人要么外出打工,要么选择其他职业,愿意静下心学手艺的寥寥无几。陈铁抓也曾试着将手艺传给家里晚辈,可孩子们要么嫌辛苦,要么觉得不赚钱,学一阵就打了“退堂鼓”。如今,他仍每天坚持编簸箕,每逢大集就骑三轮车去摆摊。“卖得不多,但够我零花了。”说这话时,他语气平和,却藏着对老手艺的不舍。
夕阳余晖漫过村庄,陈铁抓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他抱着刚编好的簸箕站在院里,目光望向村口,眼神里满是期待——他期待着更多人能闻到这缕柳香,期盼着老手艺得以传承,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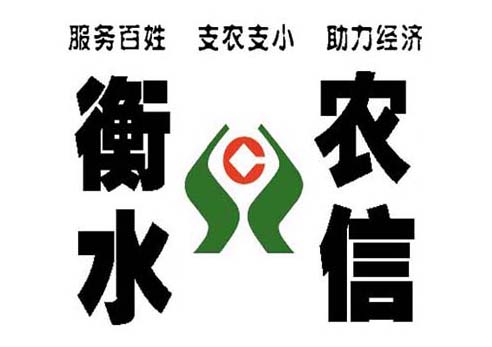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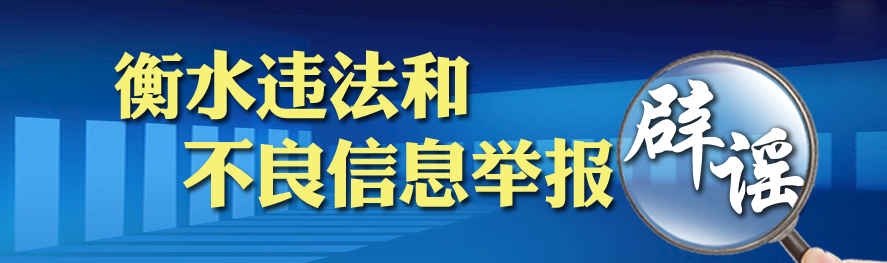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