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我梦见郝老师拧着我的耳朵往讲台上拖,醒来,惊出一身冷汗。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初中时代。那时候郝老师一直在我们乡中学教初一初二数学,不知为什么鬼魂般游到了初三改教政治,还当了我的班主任。从此,我的厄运开始了。
郝老师一副永远也不换的近视镜,身子细得像麻秆,小眼,瘦长脸,刚到五十岁年纪,活生生一个干巴老头。同学给他起外号“干枣核”。
我老家不是那个乡的。老爸从外地调来当乡长,老妈在财政所上班。我在那些农村孩子面前极有优越感,一上初中,我就成了一帮男孩子的大哥,连比我大的男生都叫我大哥,谁不听我的,准会吃我和弟兄们的拳头,谁敢告诉老师和家长,私底下挨的揍更狠。那些女生见了我,像老鼠见了猫。要不是我爸警告过,敢弄花花事就弄死我,我非得弄出一窝小兔崽子来。
还是说说郝老师吧。一开始我们根本没把干枣核放在眼里。哼!你不就是比别人多两只眼吗(加两片眼镜)?难道比我初一初二时的班主任多长一个脑袋?要知道,从前的班主任对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没把郝海明这个班主任放在眼里,想不到他也没拿我这个乡长的大公子当根葱。
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郝老师第一次给我们讲政治,声音洪亮,谈吐幽默。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却头皮发麻:这不是抢老子风头么!看到前桌邱大军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我的心脏就着了火。
邱大军是农村的,和我一起从初一升到了初三,平时我顶瞧不起他,胆小怕事,弟兄们冲锋陷阵时,他总在后面拖拖拉拉。此时,我想在他身上搞个恶作剧。他穿的那件白的确良背心成了我恶作剧的战场。我用钢笔在他后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乌龟。我又写下一行字:大王八你太会舔腚了。对我的恶作剧,邱大军不敢反抗,任我在他身上写写画画。
同桌早看见了我的杰作,笑得浑身乱颤。紧接着一屋子同学把教室掀翻了。
郝老师先是一愣,很快愤怒地扑过来,拧着我一只耳朵往讲台上拖。我试图反抗,谁知一个干瘪老头,力气出奇得大(后来听说郝老师祖上是练武术的)。我一边哎哟,一边说:“你放手,我爸可是乡长!”郝老师冷笑一声:“乡长有什么了不起,我治的就是官羔子。”说着,让我把背心脱下来,穿到邱大军身上,然后让我穿上邱大军的背心,命令我放了学穿回家去。
我当然不敢把邱大军的背心往家里穿,半路上,用小刀划了几个窟窿,扔了。
那次事件后,我老实了好多天。但报复二字不断在脑子里盘旋。
八十年代中期,学校还没让学生住校。下午一放学我就爱领着那帮小兄弟到学校周边村里去撒野。离乡政府最近的村庄叫小塔村。小塔村有一大片西瓜地,看西瓜的是一个叫傻二的小孩,十三四岁。那天我带两个小兄弟去吃瓜,傻二趴在瓜秧上,紧紧护住一个西瓜嚎叫。我们仨一边嘲笑傻二,一边连吃带扔,糟蹋了四个西瓜。临走,我霸气地说:“是学校的老师郝海明叫我们来的,你找他要钱去。”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傻二他爹领着傻二真找到了学校。傻二指着我和两个小兄弟说:“爹,是他们。”
郝老师问那四个西瓜多少钱,傻二他爹说五块,郝老师从兜里掏出十块,递给傻二他爹说:“再买你仨西瓜,要个儿最大的。”
那天上午十点钟,太阳很毒,像要把我们身上的血晒干。郝老师挤了语文老师的课,在全班学生面前,让我们仨一人抱一个大西瓜,站在操场上。又打发同学把乡长、校长、还有那两个小兄弟的家长请了来。这些人一来,郝老师一边狠狠地用巴掌搧自己的脸,一边哭着说:“牛乡长,刘校长,你们解雇我吧,我不配当老师,教出这样的学生,给学校丢人。”
这时我抱着的西瓜“啪”一声掉到了地上,我们的脸比西瓜瓤子还红。
校长把全校从初一到初三所有老师和同学集合到了操场上。我爸首先作检讨。他表示,再有下次,就把我送进号里去。
从那以后,我不再称王称霸,一头扎进书本里,像干枯的小苗狠命吸吮着水分。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后来又上了大学。考上大学那年,我爸离开那个乡调任到市里。临行前,他专门到郝老师家再三感谢。他要求我一起去,我没那勇气。
多年后,当我的孩子在学校流露出他爹当年的痞子相,老师不耐烦地说着教训家长的话,我一下想起了郝老师。当我到处打听郝老师的消息,却得知他已作古好几年。这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
大概也只有在梦里,才能再见到那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老恩师了吧。
作者:任秀红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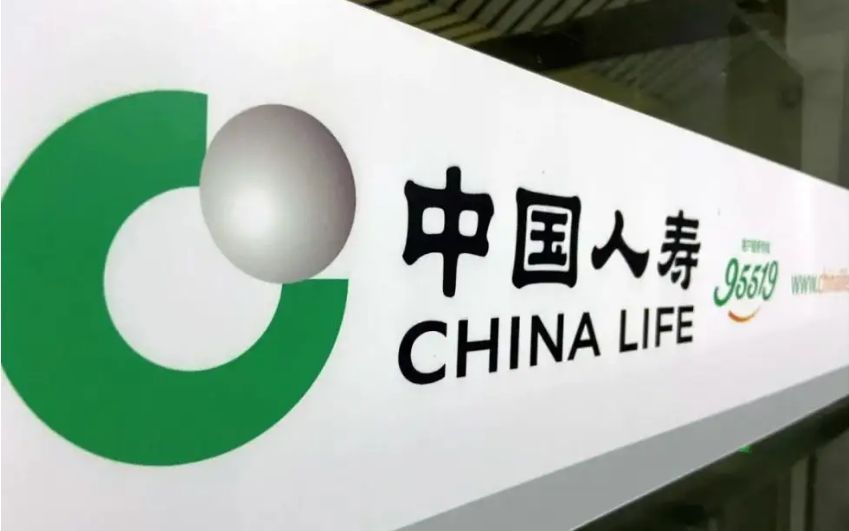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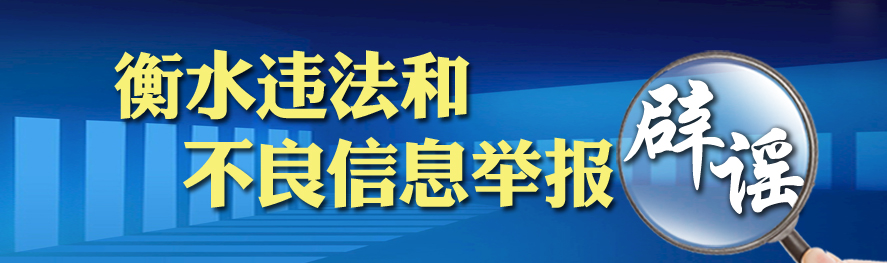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