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
常记小时候麦收时节,家家院子里,一树树翠绿的枣枝间,开满了稠密的枣花,宛如一群小小的绿衣仙子柔柔地唱、轻轻地和。淡淡的清香,熏染游子的心,相伴旅人的梦,也延展着农人丰盈的希望。
初夏的煦风轻轻吹过,放蜂人的大车吱吱撵过,细碎的枣花也簌簌的落了一巾、一衣、一地。一个尖细的小东西就钻了出来,绿绿的花萼如一把撑开的小伞护卫着它。细雨中、微风中,带着孩子的渴望,它一天天变圆、变大。七月间,枣儿就半红半绿地挂在枝条树梢,馋着你,馋着我,馋着他。
因为没有红透,也没到打枣季节,不管多么馋,也不能摘下来吃,集市上也没有卖的,即使有,在那个年代又有谁去买呢。要想吃上枣只好盼着刮风下雨了。
一场风搅雨过去,地上落了好多枣,有青有红。赶紧拣一个,来不及在蓝布褂花布褂儿上擦干净,咬一口,嘎嘣脆。有时,一口下去却咬出一条白虫子。赶紧扔了,再噗噗吐几口唾沫,虫子屎可是苦苦涩涩的。枣少时,当然舍不得扔了,小心翼翼转着圈地小口咬着。也因为有虫子的往往是最红最甜的。常想着这小白虫子还真精,专挑甜的熟的吃。直到去年才听儿子解释说,是因为虫子钻进枣后,枣里进了氧气,氧化了就熟得快,当然也就最红最甜了。那时可不懂这些,还以为虫子比人心眼多呢。边拣边吃,一会儿就吃饱了,下顿的饭也省了。
“七月十五花红脸,八月十五枣落杆。”
最盼就是打枣了,那才是吃得痛快,乐得也痛快。
常常是我们几个堂兄弟姐妹一起扛上大杆子,拿着簸箕、篓子、布袋到房后的枣树趟子里。二哥和堂哥爬到树上打高处的,年小的打下面的,不过多数时轮不上我和堂姐堂妹,女孩子只管拣枣就行了。两个哥哥正是青年小伙儿,只几杆子,枣儿就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我们捂着脑袋哇哇地笑着叫着躲着抢着。除了往簸箕里拣、布袋里装,还挑那又大又红又脆的往自个兜里塞。这时候大人是不管的,别的时候没准挨骂呢。这枣可是走亲戚过节日的重要物什。
打完了,爷爷主持着分给我家、二叔、三叔家。各家支上用高粱秸秆编成的箔,开始晾晒。虽然没有脆枣吃了,但晒到半蔫的更有一番风味,咬一口,能拉出粘粘的糖丝。尤其在屋外过了一夜的枣,凉凉甜甜可真好吃啊,每天到房上晾枣时吃一把,才真是解馋。
说起馋来,还真有一回因为枣被人骂馋嘴丫头了。
小时在姥姥家,常抱着比我小十岁的表弟玩。也是枣子半红时节,表弟非张着小手够人家树上的枣,不给他摘,他就哭。表弟可是姥姥一家的宝,平时要什么给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甚至想打谁,谁都得认他打的主儿。没办法,只好给他摘一个。心里也是怯怯的,生怕被人看见骂自己偷枣。结果是怕什么来什么,刚摘下来,就听“干吗偷俺家的枣?馋嘴!”可不就是勇哥吗,枣就是他家的。枣还在我手里,我是有口莫辩,可还是辩了一句:“是小祥要吃。”勇哥才不听我的辩解,何况他可是我们班有名的孬小子,比我大两岁,调皮捣蛋学习差,哪样都有他,这次只好任由他数落了。后来偶尔跟他闹一回别扭,他就说“偷人枣,馋,馋,馋嘴丫头!”那时觉得这简直是人生最大的羞辱,可没办法,谁叫被人逮住了呢。
我师范毕业那年,勇哥二十岁,也是在当年的那棵枣树下,他摘了好多脆枣,边吃边跟我唠媒人给他介绍的媳妇。说比他大五岁,长得不难看,就是脚上有孤拐,大概是小时候穿小鞋穿的。我笑说,你看得还挺细,还说比你大太多了,你还年轻时她就老了。秋后,他还是娶了大他五岁的脚上有孤拐的媳妇。不过勇嫂子是个会来事的人,有时我去看姥姥,她就捧一把枣过去。她大概不知道当年我和勇哥的那一番对话,要知道,没准不给我吃哩。
枣,除了脆时好吃,还可以蒸着煮着醉着吃,另外还可填到灶堂里烧着吃,那种焦糊的甜香好闻极了。来不及散尽热、剥净皮,就急急地填到嘴里,几个下来,脸都成了小花猫。
好了,好了,不写了,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完呢。
近日,那些童年少年光景,总是不约自来。如挂在青枝绿叶间的红枣,亮着希望的红灯笼,引领思绪飞一般地扑去。不只是对少年生活的恋念,更是另一种方式的期盼吧。那样无尘无滓的日子已永不会再来,所以才格外记挂。理得清,又放不下。
此时,窗外是煦暖的夏风、暗沉的静夜。我的那些枣子,我的兄弟姐妹,还有勇哥,你们都还好吗?愿这徐徐的暖风能把枣花的清香、枣儿的脆甜送到你们心上,愿每个人的生命里总亮着希望的红灯笼,暖了这世态炎凉,然后带一身轻装走各自不同的人生路,心性明净清爽,身体舒适安康!
四月南风小麦黄,
枣花未落思绪长。
浅吟轻酌忆旧事,
念罢低头空怅惘。
沽酒添灯图一醉,
只为辜负好韶光。
劝君常记少年事,
竹马青梅是旧乡。
作者:段素菊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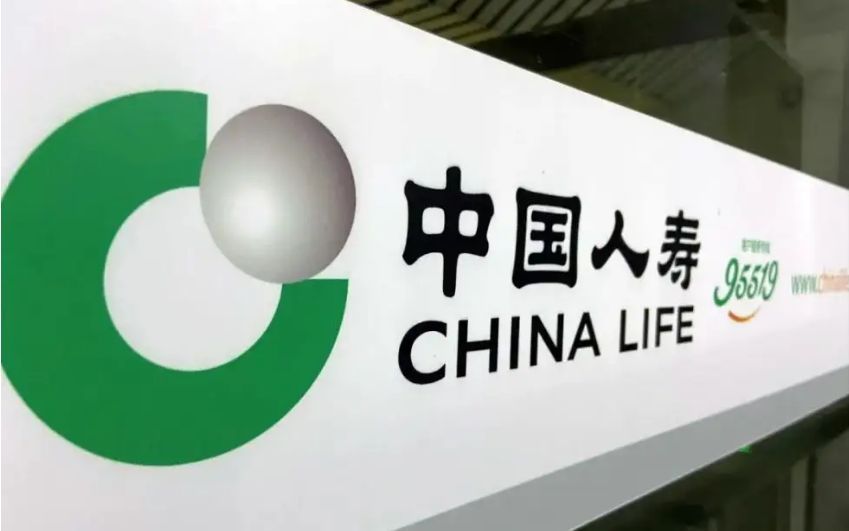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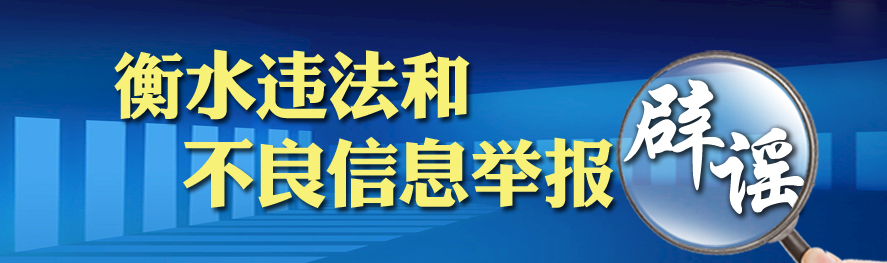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