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年冬天一到,父亲便用小拉车从县城的煤栈买来一车好碎煤。看到这一车乌黑的碎煤,母亲的脸上满是笑容,她把碎煤块儿捏在手里不住地看,只见那碎煤块儿折射着太阳的光芒,母亲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冬天煤火的温暖。她拿来一只粗孔的铁筛子,腰系围裙,猫着腰把这一车煤一筛筛地筛过,细煤洒落成堆,母亲的手上、脸上落满了黑尘。
父亲把提前准备好的黄土掺进碎煤中,土掺少了容易发散,掺多了容易炼焦,父亲根据以往的经验,用铁锨掌握着加土的比例。土和煤掺匀实后,父亲从中间往外摊开一个带沿的大盘,倒水和煤,不住地用铁锨来回翻动。和好后,让煤泥洇一会儿,母亲吩咐我们姐弟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她用手撒上筛好的细炉灰。父亲抽过一支烟后,一锨锨把煤泥倒在地上,然后蹲下身,用泥板抹平,母亲拿过铁锨,往父亲的泥板前不断地送煤泥。等到全部抹完,父亲用捅炉子的铁火柱横竖划上好多个方格子。晴天里,晾晒个三两天就干透了。
在刚抹好煤饼时,要时刻防备院子里的鸡跑上来。鸡一旦踩上去,踩上爪印不说,还会踩得院子里到处是黑煤印子。看鸡的任务一般是交给我,这个活比较轻松,我可以坐在避风向阳的窗台前,拿一根长高粱秫秸不时挥舞。等到太阳西下,鸡们倦怠地卧到墙根下或是飞到树上,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到第二天早上,那些煤泥已经定型了。
晒好后的煤块儿用瓦刀轻轻铲起来,由于铺了炉灰,脱落比较容易,父亲负责铲煤这样的技术活,我们姐弟当搬运工,把煤块放到东屋的山墙下,厚厚高高的一排,就是整个冬天取暖做饭的燃料了。
炉子是父亲用砖盘的,在堂屋的角上。由于生活不富裕,为了省煤,炉子是不会轻易点的,要看天气,要等到大风降温,水瓮结冰,才正式点炉火。每年第一次点炉子前,都要把炉子的缝隙用湿泥抹一遍。棒皮、棒核都是引火的好柴火,把煤块儿一块块掰成核桃大小,放进炉子里,不一会儿,煤块冒出火苗,母亲喜悦地做出当年第一顿冬天的炉火饭。
我最喜欢的是在炉子上烤粉条。拿一根长的粉条轻轻伸进炉火中,那粉条瞬间膨胀变白,脆香无比。在铁盖子上烤山药、烤馒头、烤红枣也都是很美味的。
在门框下的砖台上,母亲放有一把长柄的三角铁烙铁。母亲做衣服需要熨烫时,把烙铁放在炉子内烧烫,过一会儿取出后,喷点唾沫星子试试温度,觉得温度可以了,就垫上旧布片开始熨烫缝好的袄边、裤边。
晚上封火,炉膛里塞足煤块儿后,还要把筛出的小煤块盖在最上面压住,再盖上铁盖子。周遭的砖台上,烤着我们穿湿的棉鞋。我们的棉鞋不是踩雪就是汗水溻湿,都能在炉台上烤干。发面的面盆也需要放在这个炉台上。
那砖炉子是冬天里最受一家人欢迎的地方。谁从外面进来,都要忍不住先到炉子前烤烤手。早晨,我们嫌衣服凉不愿意起来,母亲总是把棉衣棉裤在炉子上烤热,然后抱在怀里给我们送到炕边,兴奋地说:“赶紧穿,别跑了热气,热乎乎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后来有了蜂窝煤,烧暖气烧大块煤,再到煤气炉、电磁炉、电饭锅、天然气、空调,做饭和取暖又快又干净。那盘砖炉子早已不在,父母也于前几年先后故去,那煤饼子炉火生活的烟火气却在我的记忆中久久停留……
作者:刘兰根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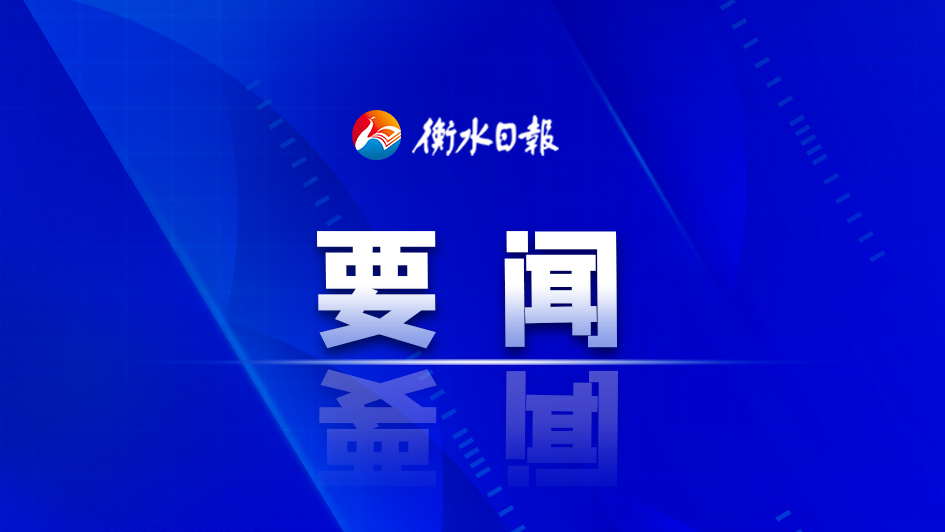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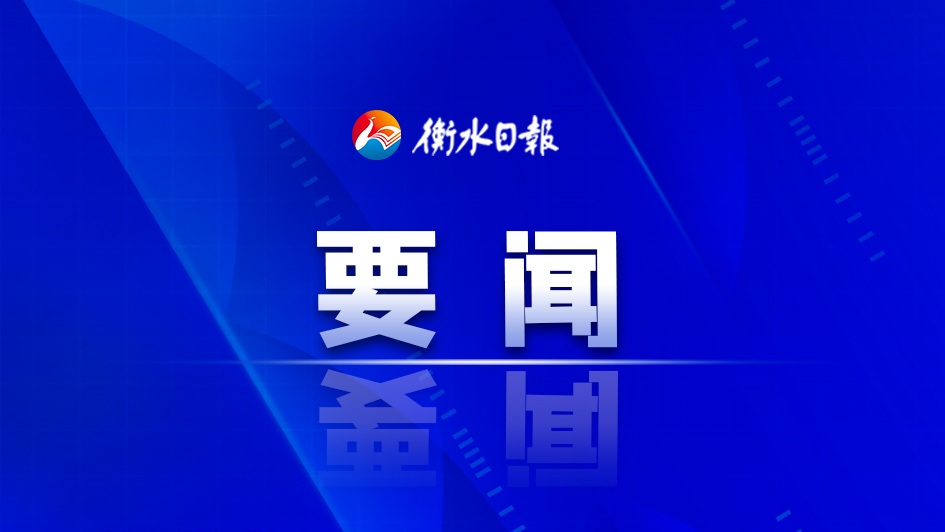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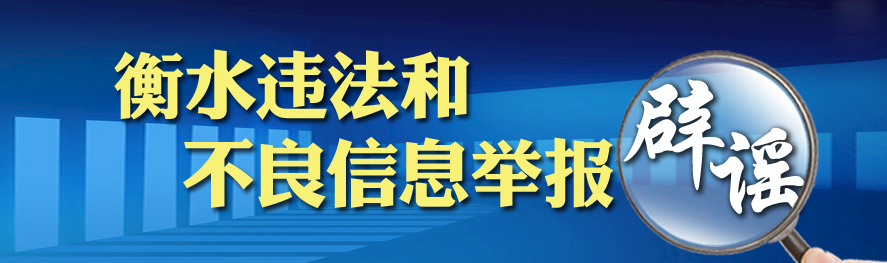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