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有一棵树,一棵普通的白杨树。它粗壮茂盛,大气端庄,挺立在生产队打麦场北面的土埝上。
土埝是滹沱河边的护村埝,与北大堤平行。随着河水改道,作用消减了,人们开始挖掘取土。埝,断断续续,几乎被夷为平地。这棵树就长在残存的土埝上,枝繁叶茂。老人们说,这是当年为防洪种下的,是仅存的一棵。虽然我们这一带不缺少杨柳,但它长在老土埝上,自然被人们另眼相看。喜欢在这里乘凉、吸烟、歇地头。也是队上派工、开会的地方。
树北面的一方地是队上的“保命田”,近水好肥都用在这块地。钟声一响,大家都聚在树下,悉听队长吩咐。老杨树见证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见证过劳动竞赛的火热场面,也洞察了生活的另一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员到队上参加劳动,出现了“混工”的说法。听到上工的钟声,先要在树荫下懒洋洋地抽一锅“地头烟”;有人随身带来了牛子牌(一种赌博的工具)、扑克,开始玩“拱小牛”“拱猪”;女人们有的纳鞋底儿,有的织毛衣,也有的闭上眼睛睡大觉。
我当年高考落榜后,曾到生产队“混过几天工”,但既不会“拱牛”,也不会“拱猪”,属于另类。有人从外地捎来一本刚出版的小说《生活的路》,反映知青生活的(忘记了作者是谁),正好靠在杨树上读小说。
记得一次有位老人从此路过,看不惯社员懒散的样子,扯开嗓子喊:“太阳晒着啦!太阳晒着啦!”意思是时间不早了,该干活了。
“拱牛”的动了动地方,依然拱着,玩着。
树荫大,乘凉的人就多。生产队议事在这里,闲话谣传在这里,哄孩子的老太太也常常一手领孙子一手牵羊,孩子在树下玩土,羊在旁边啃草,“革命生产两不误”。
麦子上场的季节,社员们常在树下放一桶井巴凉水,渴了就蹲下身子,吹掉扬场落进的麦糠,大口大口地喝一气。有些冒失的小伙子,只顾喝水,脸和鼻子都蘸在水里,老人们就会在其屁股上打一把掌。轮到自己,照喝不误。白杨树临着大道,做小买卖的、过路的外村人,也时常在此逗留喝水,寻人问路,说笑如归。
傍晚,太阳从远方照射过来,将老树染成金黄。晚风摇动着树梢,树叶子刷刷作响,像鼓掌、像大笑,像一位沧桑的老人,居高临下,手捻胡须,审视着村庄发生的事情。
麻雀在这里集结,它们晚上要住在这儿。仨一群俩一伙,先在附近的庄稼上、草丛里逗留观望,等人慢慢散去,周边清静了,才试探性地落在树上。到晚上,满树都是麻雀。估计和相邻的打麦场有关。麻雀们也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
雀们选择在这棵树上落脚,虽占据了“风水宝地”,也经历过一次天灾。一个夏日的晚上,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成为鸟群的灭顶之灾。次日晨,看场的老刘头足足捡了两大筛子麻雀。
冬天,北风刮走了树上的叶子,草也枯了,麦场也干净了,周边一片萧条。麻雀们搬家到村里,几个拾粪的老头常聚到树下。他们把粪筐粪叉一放,靠在土台的阳坡上,点着烟袋锅子,有说不完的话。偶尔,有一群孩子跑到麦场打陀螺,鞭子甩得啪啪直响。老树不寂寞。
1985年10月,我当兵复员回家,到村口时第一眼就看到老白杨。它高高地挺立在土台上,风一吹,树枝不停地摇啊摇的,深情地和我打着招呼,似有话要说。弟弟告诉我,土地大包干以后,地分到了各家各户,队上的打麦场被分成若干个小块,有的起土垫了庄基,有的依然作打麦场。不吃“大锅饭”了,人们可勤谨了,争强好胜地过日子。谁也没空在树下扯闲篇了。
现在,这棵树分到了我家名下。
一天,我来到树下,踮着脚登上土台,杂草丛生,不少破砖烂瓦堆在那里。显然好长时间没人来过了。我突然想起了生产队开会的情景,想起了当时的热闹场面,想起了“拱牛”“拱猪”的社员们,想起了那本《生活的路》……
站在土台上,向东眺望,远处是南吕汉村的旧址。儿时的夜晚,那里总有几盏灯火。为了避水,多数村民搬到堤北,只剩下几户人家。依稀记得那几处散落的土坯房。有位肩背粪筐身穿一身粗布的老人,屁股后面总跟着一个半大小子,弱智,名“瓜”,穿着自家染的蓝布衣裳,常将手指含到嘴里,拼命地追赶被风刮跑的“滚蛋棵”。坯房西侧有几棵垂阳柳,掩盖着一片坟地……像极了一幅俄罗斯油画。
时光荏苒。目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蔬菜大棚,是“饶阳县百里绿色长廊”。棚内的葡萄一嘟噜一串儿,像翡翠、像珍珠;蔬菜瓜果,碰鼻子香;北面是“蔬菜育苗基地”,育种、发苗、管理,全程电脑操作;方田林网,修上了公路,四通八达;东边的瓜菜市场停满了拉菜的汽车。客商、菜农打箱装菜,忙得不亦乐乎;市场上空飘扬着五星红旗,喇叭里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真是新时代,新气象。
一位老奶奶问我,土台上的老树像什么?我说像酒杯,土台是杯座,树身是杯腿儿,上面盛满了葡萄酒。她摇摇头说,那是你们“酒人”的眼光。我看像个香炉——“烧着高香”。说完哈哈大笑。当然都是玩笑话。
玩笑归玩笑,几十年过去了,树下的人事鸟事沉淀在我的记忆里,总也挥不去。
作者:刘善民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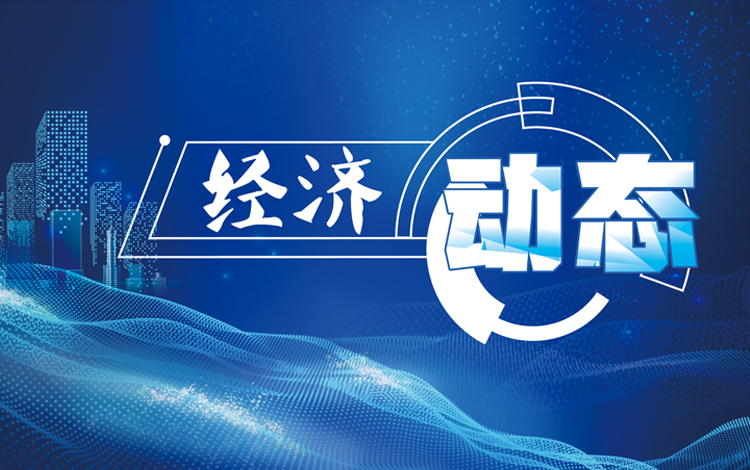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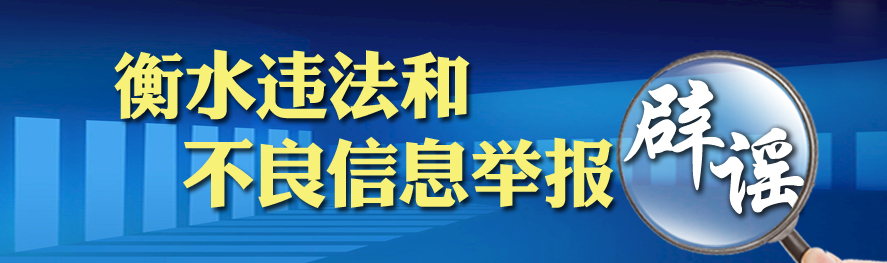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