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抑郁了。那是一个春天,一个被寒冬坚冰拖垮的春天,我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只剩了哭。
朋友为救我,又是买票又是贡献行囊逼我去了遥远的海南。23天行程,自我感觉良好,一回到北方,旧病复发。爱人买回的粉色小药粒没起什么作用,网上购买的十几本心理书疗效甚微,甚至三位心理师也没能将我彻底还原成过去那个幸福感爆棚的傻女人。多怀念那些没心没肺的日子啊,整天想着感动全世界,不求回报,怎么忽然就计较了呢?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不想出门,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有一点好处就是能够在书房中长时间沉醉于文字了。或许缘分吧,《灿烂千阳》这本书恰巧映入眼帘,书名让我眼前一亮,最需要阳光的人啊,多期待被一千个太阳温暖。据介绍,卡勒德·胡赛尼的作品全球销量超过4000万册。
作品中第一句话有个词引起了我的好奇,“哈拉米”什么意思?五岁的玛丽雅姆第一次听到,我也是。原来是“私生女”的意思。是玛丽雅姆的母亲在骂她,只因她不小心打碎了一件中国瓷器。母亲也经常偷骂父亲。玛丽雅姆不爱刻薄的母亲,她最爱的人是父亲,可惜这个赫拉特大富翁每周四才过来看她陪她那么一小会儿。她多渴望能像父亲的另外十个孩子一样,去父亲的影院看一场电影,到父亲家住一晚,可惜她在阿富汉是不合法的,是父母的耻辱。她一直不知道自己耻辱到了什么程度,直到十五岁时提出跟父亲走,被拒绝,她一个人在父亲家门外苦等一夜也未被接纳,明明在家的父亲(隔着窗帘她都看见了)派司机强行把她拖回母亲嘴里的“老鼠洞”,直到透过风吹起的窗帘般的柳枝看到吊死的母亲,才知道母亲一直是对的,才后悔自己不肯听母亲的话有多愚蠢,自取其辱的结果就是父亲在全村人面前做样子将她接回家,然后快速将她许配给六百五十公里外一个年近半百的老鞋匠拉希德。此后,门外是战争,门内是暴力,一个孤儿般的女孩子怀着耻辱愧疚心,在喀布尔渡过了十八年没有尊严和爱的日子。更残忍的是,老酒鬼拉希德又趁战争之危,将一个被炸死双亲的十四岁女孩莱拉娶进门内,只为获得一个儿子,全然不念玛丽雅姆多次流产不能做母亲的痛苦。玛丽雅姆和莱拉本是不共戴天之仇,但她们很快成了朋友,像亲娘俩,甚至更亲,因为有着太过相似的命运。是的,一个哈拉米,一个高材生,本该有着不一样的命运,但塔利班命令妇女一律不得工作不得读书不得单独外出等等,她们一样了。尤其拉希德用卑鄙谎言骗莱拉说她男友死了,她这才怀着男友的孩子匆忙嫁给可以当她老爷爷的鞋匠。老鞋匠猜出原委后,对哈拉米女儿百般虐待,甚至逼莱拉将其送至恤孤院。他晚年的爱全部给了迟来的小儿子。两个女人在轮番挨打受尽羞辱后准备出逃,但遭到连杀人放火、强奸偷盗都不管的警官“维持秩序”的提审,莱拉泪如泉涌,回家被丈夫打死活该,想活命就违反了国家秩序,这就是阿富汗女人。果然,恶魔甩起了鞭子,他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他预备打死这两个“忘恩负义”的女人。眼看着莱拉被掐死,玛丽雅姆情急下抄起铁锹,将老鞋匠拍死了。为成全莱拉一家,玛丽雅姆一个人走向了监狱,并提出不许任何人探视。莱拉与男友有情人终成眷属,带着俩孩子逃到早已超过两百万阿富汗难民的巴基斯坦,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1973年,是玛丽雅姆失去母亲、嫁给老恶棍噩梦般的开始。2003年,是莱拉重返阿富汗探寻旧情、当上老师崭新的开端。莱拉始终不知道玛丽雅姆埋在哪儿,觉得她无处不在,“最重要的是,玛丽雅姆就在莱拉自己心中,在那儿,她发出一千个太阳般灿烂的光芒。”在故事结尾,莱拉又怀孕了,一家人忙着取名字,最后一句让人温暖而泪目,“但这个游戏只和男性名字有关。因为,如果是女孩,莱拉已给她取好名字了。”
作家笔下的三十年,恰巧是我生命的前三十年。我知道,人的出生地是不能选择的,但地球仪稍一倾斜,说不定就会滑到哪个倒霉国家,万一是阿富汗呢,那样我连抑郁的自由大概都没了。
终于明白,抑郁最大的祸患不是心理专家口口声讨的原生家庭,也不是从前自己追求完美想当圣人而不幸遭遇的遇人不淑,最大的祸患就是闲得太难受了,这是一种富贵病,一种矫情病,一种“给你自由过了火”的病,一种吃饱了撑得太难受的病。我问我妈,“三年自然灾害,咱村一天抬出去八个,有没有人想到过自杀?”我妈坚定地摇头,“那时候人们天天想着哪儿有口吃的就好了。”
一碰就折是面条,百折不挠方为钢。
玛丽雅姆和莱拉,从没顾及过身上的伤,心里的疤,她们关心的只是活命,即便这么简单的需求,都是奢侈。我何其幸生在了男女平等的国度,嫁进了没有暴力的家庭,有一间安静的书房,可以安放我靠自己工资得来的无数名著,容纳我虚胖的理想抱负,总之,自由无处不在,我的心灵可以高歌,双脚没被困住,我夸大了自己的不幸,挡住我的并非一座山,只是一粒沙,我却躲进黑暗自甘堕落,这不是白白浪费光阴么?
最重要的是,玛丽雅姆也已经在我心中,还有莱拉,在那儿,她们发出一千个太阳般灿烂的光芒,给了我战胜寒冷的勇气和良方。
作者:魏东侠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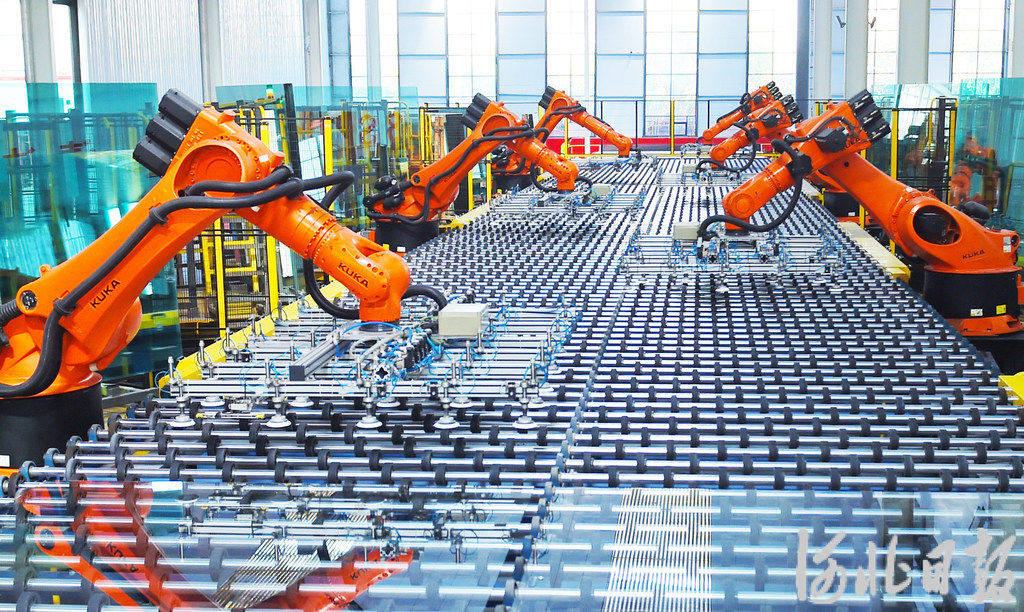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