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对人是一种依恋,人对燕有一种情怀,人燕相邻是天然的默契。
喜欢这精灵不在于它的乖巧灵秀,也不在于它的燕语莺声,只在意那份对家的专注、眷恋和不舍的深情。
记忆深处,当杏花吐蕊、杨柳报春的时侯,奶奶总把屋门上头的窗纸捅开,留出进门的通道,高兴地说:“咱家的燕子快回来啦!”
不久,或在午后的不经意间,或在黎明的梦景里,便会传来燕子的歌声。此刻,我常常跑到屋外,在空中寻觅,寻找那久违的身影。它们有时立在房檐,眺望家门;有时爬上窗棂,呼唤乡邻;有时俏然于电线上,顽皮地和我们打着招呼:“嘿,我回来啦!我换了一身新衣裳!”我开心地望着那黑色的礼服:颈下的白领、尾端的剪刀和那个涂有黄色胭脂的喙。冲它们招招手。它们笑着,叽叽喳喳地讲述一路的风景。欢声笑语透露出回家的喜悦。
滹沱河岸边的村庄,虽世代农耕,却也不乏在外流浪的人。他们正像这些燕子,无论飞到天南海北,总割舍不断那份家的情怀。
我母亲的爷爷是个能工巧匠。据说,年轻时在南方曾参与某个皇陵的修建工程。他有文化,熟识图纸,精于设计。被招工之后去了南方,多年却杳无音讯。若干年后,有人捎回一个包裹,除几件衣物外,是一摞无法投递的书信,字里行间浸透了思乡的泪水。原来,工程方利用他的技术,扣压多年,不让回家,直至客死他乡。一个亡故之人的包裹,经老乡的几经辗转,为其寻找家门,不丢弃,不放弃,最终回归故里。此中所蕴含的乡情和那份家的情愫,至今想来,感激涕零!
在久远的年代,交通不便,又没有通讯,“捎口信”是唯一的联络方式。那些受托捎口信的人,携带的是游子漂泊流浪的心。因而,他们信守承诺,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乡间土路,去寻找一份心灵的归宿。有时就是报一声平安,传递一个信息:“还活着”。然而,就这简单的三个字,足以让家人欢呼雀跃,让年迈的父母热泪纵横。
滹沱河有个传统,无论是外出经商或是作官,家里一定要留一处老宅子。或托人管护,或用砖把门封好,以备将来叶落归根。在封堵门户时,都会在门的上方留一个小洞,那是燕子回家的路。有的燕子归守故道,有的却离开房梁,在屋外的檐下重新筑巢。但无论把巢建在哪个位置,都不会离开老宅子。
我们时常慨叹世间的人走茶凉,抱怨生活中被遗忘冷落的细节。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在这老宅旧巢的寂寞里,听一曲归燕坚守的鸣唱,闻一把土墙老硷的淡定,便会在顿悟之中渐入一方禅境。
回家是一首歌,也是一部书。演绎着岁月的沧桑巨变,也囊括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春节,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村庄,只为吃一顿年夜的饺子。
清明,人们点燃思念的纸币,只求一点心底的慰藉。滹沱河的水断断续续,但河边祭祀的烟火却不曾断过。子孙满堂者当然香火旺盛,而每次上坟却不忘给那位光棍老汉一把纸钱。儿时的故事里,总有他的影子,给他一点钱吧,尽一份乡邻之意。
公墓里,时常出现陌生人的碑位,那些远在他乡的亡灵,临终有遗志,魂归故土,安然。
1996年夏天洪水期间,我曾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打来的。他说,每天守着电视机,眼望受灾的村庄、被洪水围困的乡亲和坍塌冲走的房屋,心像刀剜一样。年纪大了,不能回村,一定要向乡亲们转达问候。言语之间,声音哽咽,令人感动。后来得知,他虽远在外地,却积极组织捐款捐物,默默地为家乡贡献着自己的余热。
写到这里,想起了蓝天野的一首诗:“离家七十载,今日得还乡,天涯多芳草,最美是饶阳。”
这首诗是1998年10月蓝天野回饶阳时赠予原饶阳县政协副主席何同桂先生的。
何同桂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是说:“午餐安排在县宾馆。为体现故里特色,我嘱咐准备了薰肠、烙饼、炸小鱼、杂面汤,还上了衡水老白干和本县的胡萝卜汁……蓝老的诗是写给我的,也是写给饶阳的。这是一个远方游子对故乡的赞美,也是一个德艺双馨文艺大家对桑梓的祝福。”
老人是滹沱河的燕子,从艺多年,漂泊天涯。时感疲倦时,偶一回头,发现这滹沱河畔的稗子草和燕子窝,闻到了秫面饼裹小鱼的清香。于是,一挥手杖,感慨万千:离家七十多年,还是滹沱河的鱼香……
作者:刘善民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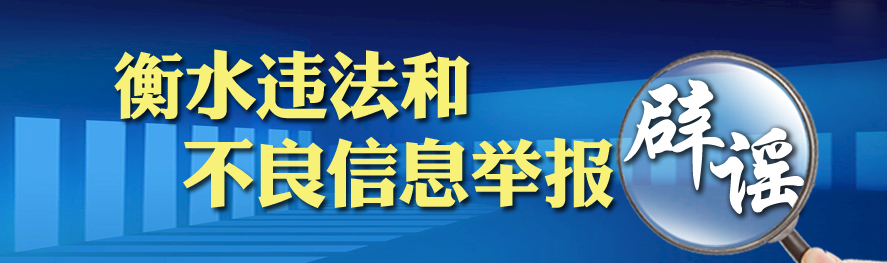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