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衡水武邑县一间飘着木香的工作室里,直径40公分的牡丹浮雕上,刀锋正与木料“私语”。木屑簌簌飘落间,80后木雕艺人武冬冬屏住呼吸,将刻刀精准切入花瓣脉络——这是他与木头对话的第25个年头。从农村少年到非遗传承人,他用一把刻刀,在工业化浪潮中凿刻出传统木雕技艺的新生命。





少年与木雕的初遇
1984年出生的武冬冬,与木雕的缘分始于少年时表哥家的窗台。当他第一次看到窗台雕花木料上栩栩如生的花鸟,瞬间被深深吸引:“表哥说那是家具装饰,我当时就着了迷。”从此,他从磨刀认木纹开始,跟随表哥学习欧式雕花基本功。但,少年心中的火焰并未满足于此,“我想雕出会说话的人物,雕出能看见故事的山水。”这份执着,驱使他踏上了漫长的学艺之路。
从天津到北京的十年苦学
2000年,初入天津的家具厂车间,年轻的武冬冬就感受到了木雕技艺学习的艰难。为了练习运刀,他常常将刻刀顶在腋窝下,在闷热的夏夜中反复操作。“凹槽深浅差半毫米,图案就会走形。”武冬冬深知其中的关键。为了精准控制力道,他经常熬夜到凌晨,在台灯下对着一块普通木料练习上千次下刀。单薄的工装被汗水浸透又风干,腋窝处的皮肤被刀把磨破结痂,最终形成了厚厚的老茧,但这些都没能磨灭他对木雕的热爱与坚持。
听闻北京能学到更精湛的木雕技艺,21岁的武冬冬满怀憧憬地踏上了新的征程。在北京的10年间,他为了接触不同的雕刻工艺,先后辗转很多家具厂。其中,24岁那年的经历让他尤为难忘。当时,他刚到一家新厂,厂里接到一批红木顶箱柜的订单,要求在箱板上雕刻人物。对于当时人物雕刻尚显薄弱的武冬冬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他既兴奋又忐忑。然而,现实却泼了他一盆冷水,没有一位师傅愿意对他倾囊相授。但武冬冬没有放弃,他选择在师傅们传授技艺时,偷偷站在一旁观察,学习他们的用刀手法;在别人休息时,他依然留在厂房内,仔细揣摩雕刻师傅作品的构思与刀法。
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武冬冬,没有一点绘画基础,所以制作木雕对他来说并不容易。“画画是做木雕的奠基石,有了画画的基础,我才能雕出逼真的作品。”因此,武冬冬买来大量美术书籍自学,他还到美术馆看展览,通过电视听专家讲解……甚至在吃饭时用筷子在桌面上练习线条,一步步弥补绘画基础的不足。
七道工序让木头焕发生命
如今的武冬冬,早已褪去了当年的青涩,成为木雕领域的行家。他的工作室里,几十把刻刀整齐排列,如同等待出征的士兵,每一把都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从选材、手工绘图、贴图纸、出大型、修光、打磨到上蜡,木雕的七道工序在他手中环环相扣,严谨而细致。就拿他正在雕刻的牡丹浮雕来说,从原木到成品需要整整一周时间。“选料要顺纹,这样雕刻时木料才不易开裂;绘图要应形,根据木料本身的形状和纹理构思图案;修光时最关键,连花瓣的经络都得赋予生命力。”他一边雕刻,一边认真地介绍着,眼神里满是专注与热爱。


在众多雕刻题材中,人物雕刻是武冬冬的“拿手好戏”。为了让木雕人物“活”起来,他下足了功夫。日常生活中,他会反复观察不同年龄、不同姿势的人物神态特征,将这些细节铭记于心。雕刻微笑时,他精准把握苹果肌的弧度和嘴角上扬的角度;刻画蹙眉时,连额角皱纹的疏密走向都要经过数十次调整。“人物雕刻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要把精气神刻进木头里。”他指着工作室墙上的人物图纸说道,图纸上的人物或抚琴或酣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能从图纸上走下来。
让非遗在创新中新生
多年的努力与坚持终于让武冬冬从武邑县的能工巧匠,成长为全国家具雕刻大赛的“工匠之星”;他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其木雕技艺也入选了县级非遗名录。如今,他声名远扬,不仅当地人找他制作木雕,北京、天津、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市的雕刻厂也纷纷前来与他开展技术交流合作。然而,在众多荣誉面前,武冬冬依然保持着谦逊与初心。他的案头始终摆着一把“不满榫”的老斧头,时刻提醒自己:“榫眼永远填不满,技艺也永远学不完。”这把斧头,不仅是他谦逊的象征,更是他对极致技艺追求的体现。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爱上木雕这门传统艺术,武冬冬不断尝试创新。他创作的《冰墩墩》木雕作品入选河北非遗优秀作品,正是传统工艺与现代元素结合的成功尝试。“希望年轻人看到,木雕不只是老手艺,更是能与时代共鸣的艺术。”他满怀期待地说道。
当夕阳的余晖洒在工作室,武冬冬的刻刀仍在木料上穿梭。木屑纷飞间,牡丹花瓣渐次绽放——这是一位匠人的坚守,更是千年木雕技艺在新时代的生动注脚。在工业化浪潮中,武冬冬用一把刻刀,守护着非遗文化的根脉,也雕刻着属于传统手工艺的未来。
见习记者 王亚楠 张今越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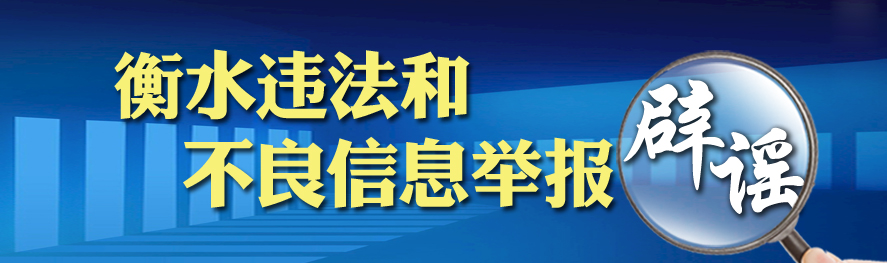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