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的夏天,每到麦收前,母亲总是要去赶一次集,除了麦收用的农具和食物,母亲还买回来三两把蒲扇。
家里人口多,不能保证人手一把新蒲扇。新蒲扇淡绿色,有植物的香气,经年的蒲扇变为枯黄,有柴烟的味道,变得易脆裂。边沿处开裂的地方不少,为防止划手,母亲把蒲扇的边沿用旧布包了一层边。
土坯房子冬暖夏凉,在那没有电扇的年代,一把蒲扇就能度过一个夏天,蒲扇的风柔和凉爽,扇累了,把扇子扔到一边,香甜地进入梦乡。
母亲很少用扇子,她觉得扇子是闲人的标志,母亲也没有时间闲下来扇风。她每天起早下地,八九点钟才回来吃早饭,然后再去地里,直到晌午才回来。母亲洗去汗水和灰尘,然后和面烙饼或是擀面条,忙活一家人的饭菜,等到我们陆续进家,总能吃上现成饭。
那时候常有邻居们来串门,遇有坐下来聊天的,母亲总是伸手递过扇子,父亲则第一时间沏上茶叶水。在他们看来,扇子和茶水就是最高的礼遇了。
我们的中午饭常常在大门过道里吃,过堂风很凉快,影壁墙前的大槐树树荫浓密。我家住村口,每天从门口路过的人络绎不绝,父亲母亲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一顿饭吃下来,不知道能遇到多少人。有的孩子在门外徘徊,家里大人下地还没有回来,母亲就让他们坐下来,递过一角饼或一个馍馍,让他们边吃边等。有一次母亲正切西瓜,碰到隔了几个胡同的三爷爷路过,忙让三爷爷吃西瓜。三爷爷边说着“不不不”边回家走,母亲匆忙切下一块儿西瓜,竟忘了放下手中的菜刀,一手托着西瓜一手提着菜刀撵三爷爷,一直追到三爷爷家的胡同口才追上。母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三爷爷非常不好意思地接过了西瓜。回来后,母亲说三爷爷是实在人,前几天还帮咱们家修了电灯的开关。母亲的脸上淌着汗珠,拿起扇子扇了几下,像是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似的,露出欣慰的笑容。
晚上,清扫过的院子里洒上了水,暑热退去,饭后拿一把扇子躺在地上的布包袱上,惬意无比,不但凉爽,还能驱蚊子。母亲常常扇不了几下扇子,就睡着了,她从早忙到晚,实在是太累了呀。
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她有着朴素的劳动观念和善良大方的实在心肠,从不娇气,以“铁姑娘”为偶像,以干活多、力气大为自豪。
后来家人外出做小生意,母亲舍不得用煤气,一直用煤炉做饭。炎热的夏天,厨房的炉子也没有停过。每次我回去,母亲总是在炉子旁做“差样儿”的。放上小铁锅打水煎包,火焰总是上不来,母亲就往炉膛里放进一两个棒核,父亲坐在旁边的马扎上拿一把破扇子扇风,锅里的火候一会儿需要大火一会儿需要小火,母亲不断地指挥,父亲不错眼珠地盯着火苗。一锅金黄的水煎包终于出锅了,那充足的韭菜猪肉馅透过面皮,浸着油汁,香气扑鼻。父亲一扫刚才扇风的烦躁,擦擦脸上的汗水和呛出的眼泪,喜笑颜开地说:“你娘就是手艺好,这水煎包要是在以前,是赶集串在高粱莛上卖的。”母亲赶紧补充一句:“那时哪里舍得吃纯水煎包啊,得用大饼卷起来吃,俺村里有个老太太赶集回来装了两根高粱莛,儿媳妇大闹不止,高粱莛上有油印,说明老太太在集上自己吃水煎包了,没有拿回来。”
经济条件不好时,吃一顿水煎包不容易,经济条件好了,夏天的暑热,也是不适宜吃水煎包的,烟熏火燎,汗流浃背。可是父母的那份兴奋,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只是因为想让他们的女儿回家后吃上一顿拿手饭。
伏天里,家里终于安了一台空调,没两天,在外地的姐姐回来了,因为刚做了一个小手术,父母又从空调间里搬出去,让姐姐在空调间里修养恢复。等到姐姐痊愈恢复,秋天到了,空调也不用开了。这年的秋后,父亲突发疾病,故去了。弟弟接手了门店的生意,母亲回到了老家,住在弟弟的房子里。卧室有一台空调,母亲只是偶尔开,对于电器,母亲除了怕费电,更觉得累心,一把蒲扇,让她更有亲切感。扇风驱蚊,母亲在重复的动作里,排遣内心的孤寂与病痛的折磨,三年后,久病的母亲也故去了,刚刚60岁出头。
从20岁时嫁过来,拉扯大我们姐弟三人,母亲的生活中一直都是节俭。成年后的我每买一件新衣,必被母亲数落好半天。她的概念是,有穿的,就不能买新的,没穿坏,就不能买新的,穿裙子就不是老家人的做派。以至于那些年里,在城里工作生活的我,回老家时只穿旧衣,夏天回老家从来都是长裤。回想起来,贯穿母亲40余年夏天的,是一把蒲扇,或新或旧,用或不用,一直在身边陪伴。
“粉落空床弃,尘生故箧留。”久不住人的老家,母亲的许多旧物仍在,那把蒲扇,早已布满灰尘,纹理依然清晰,像是一道道特殊的符号,记述着母亲那些年夏天的点点滴滴。
作者:刘兰根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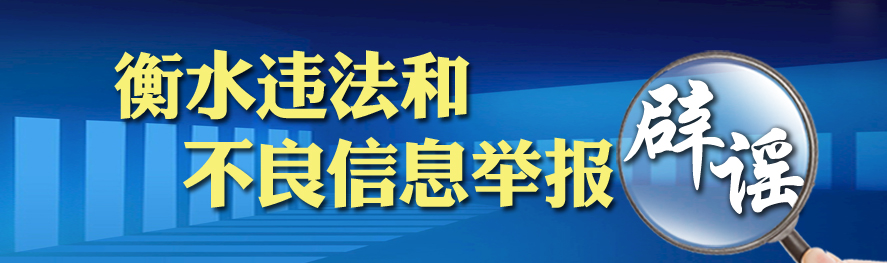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