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把兰钵大爷视为自己最知心的朋友。父亲喜好结交,在小小的县城里可谓朋友遍天下了。但在父亲心中,兰钵大爷是无可替代的。
兰钵大爷姓张,比父亲大了一岁,属马。兰钵大爷老家是衡水县(现桃城区),如果不是共同考入冀南建设学院(读书期间学校又恢复原名冀县师范),他们俩几乎没有认识的可能。同学之中,二人因为志趣相投,遂成了一生的知己。
1951年7月毕业,父亲回到武邑城关完小任教,兰钵大爷分配到地区行署。可能是兰钵大爷不喜欢行政工作,也可能是他身边少了朝夕相处的好朋友,没过多久,他竟主动要求从行署机关调到武邑完小当一名普通老师。父亲曾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一情节,为了兰钵大爷顺利调动,他还专门去找了武邑主管教育的领导。这样他们俩又成了并肩携手的同事。那时父亲和兰钵大爷都是县城里风头正劲的人物,体育成绩好,在全县体育大会上摘金夺银,风光无两。篮球又打得棒,唯一的灯光篮球场上,他们身手矫健,配合默契,战无不胜。其后他们一同进入武邑中学,大大小小的运动接踵而至,他们的友情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考验。直至后来学校停课,他们才分别下放。父亲回到老家,兰钵大爷回到了衡水。1972年父亲调回县城参与体委创建,而兰钵大爷一直留在桃城区从事教育工作,先是衡中,而后调到桃城区教育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因病提前办了离休,后为照顾二姐生意,也和母亲来到了市里。这样他们又和在桃城区工作的兰钵大爷经常见面走动了。只可惜九十年代中期,兰钵大爷在一次会议上突发脑溢血,虽经过艰难恢复,但身体还是留下了行动不便的后遗症。于是父亲会和母亲一道从西向东穿越一座城市去看望老朋友,有时也会禁不住兰钵大爷的再三挽留在那里留宿。这样老哥俩又可以像年轻时那样躺在一张床上聊个通宵。
最近,我从父亲生前珍藏的小皮包里看到一篇手写的文章。虽然我不认识兰钵大爷的字体,但从这一篇没有署名、不具日期的短文内容来看,确属是兰钵大爷写的。文章大概就是写在那个时期。
篇名《益友》,现抄录如下:
贾桂其——是我的莫逆之交。系武邑县马回台乡贾史庄人。他身材匀称,体型完美,堪称一潇洒、英俊男子。
在冀南建设学院同学二年,我们生活上互相关心,学习上互相帮助,晚上睡觉钻一个被窝。我们俩都喜欢打篮球,他也擅长跳高,球类、田径则是我的所爱。每逢学校开运动会,我俩都是场上的活跃分子——他跳高,我投弹。
课余时间我们常在一起打篮球,还不断在一起切磋球艺,取长补短,这更加深了我们彼此的友谊。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武邑县城关完小任教,我被分配到地区行署。一个月后因承受不了生疏而繁重的工作,志愿去武邑县城关完小任教。我俩又由同学变成了同事,在他的推荐下,王郁州校长让我当了该校一名体育教师。这时我俩的关系也更加亲密。
相同的爱好、共同的志趣把我们俩的心紧紧地系在了一起,我们形影不离,穿衣服时,也是同样的布料、同样的颜色、同样的款式;理发时,连发型也是一样的,有些学生竟分辨不出我俩的姓名,说来真是有趣!
光阴荏苒,转瞬间我们都由欢快的青壮年变成了耄耋老人。
风云变幻、斗转星移,几十年来,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仍是互通电话、互道平安。走访、探视、聚会,一年中总有几次。我们交流养生经验、长寿之道,谁有困难仍像当年一样互相帮助。
我们的友情绵长、厚重,冰清玉洁,终生难忘。绵延了60多年的友情,就像松柏那样长青!
算一算父亲珍藏这篇文章应该有十多年吧,而父亲离世又过了十年有三。三页普普通通的稿纸,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父亲心中有多么珍视这一份友谊!
父亲去世的那几天,据兰钵大娘说,兰钵大爷抱病在床上大哭了一回。其实他的身体也已经非常虚弱,根本没有气力大哭了。大哭过后,兰钵大爷的眼睛始终是泪涔涔的,擦都擦不干爽。他整日坐在屋里,不同人说话,一双泪眼望着空洞的地方发呆。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我和弟弟去看望兰钵大爷。刚一进门,兰钵大爷坐在沙发上看到我们,一张脸便难过地抽动起来。我一把抓住兰钵大爷的手,很担心情绪过于悲痛会伤害他的身体。最好的朋友离开了这个世界,自己的生命也被割掉了一半。这是兰钵大爷当时留给我最深的体会。
几年之后,兰钵大爷也去世了。泉下故人多,父亲和兰钵大爷这对一生的知己又见面了!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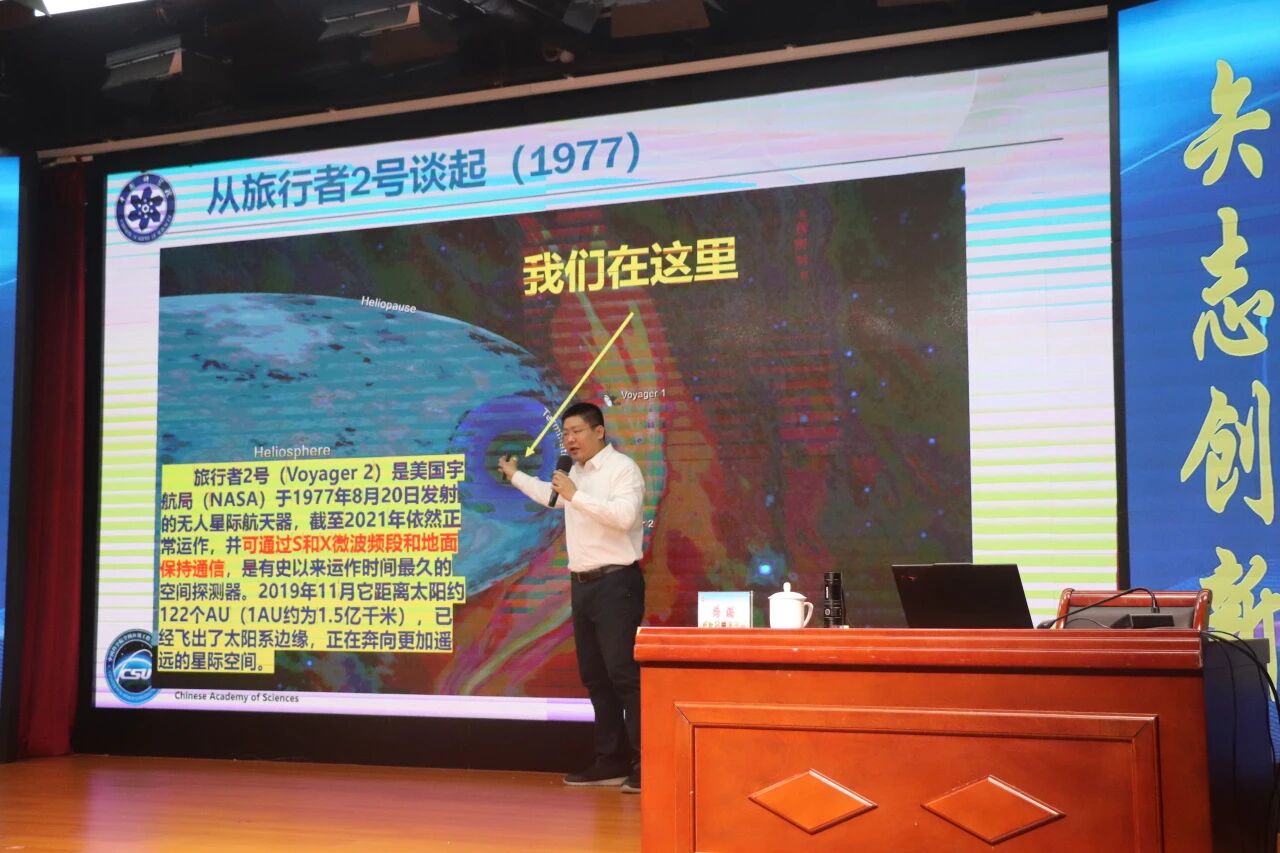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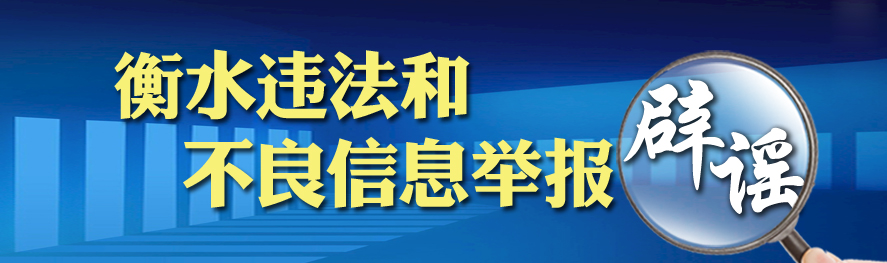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