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家庭档案,找到田秀川先生生前的三十六封信札,逐件仔细翻阅,又如当面聆听先生那推心置腹的轻言热语,不禁泪眼模糊。
田秀川,笔名田人、田野上人,是衡水的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也是知名作家和诗人,曾出版发行自撰诗词的书帖十几部之多。
我与先生,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研讨会。那些年我们曾同居一室彻夜长谈,也曾相约小酌诗文佐酒。所以他虽长我十九岁,却因性情相投,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
先生常称自己“素喜笔谈”,生前经常给我写信。尽管后来有手机也互通微信,但他仍经常靠信札与我倾吐心声。人们常称作家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那先生就是最后给我写信的一个文学前辈。
我现存他的三十多封信札,是我们纯真友谊终生不渝的佐证,更是我在历经沧桑人海浮沉中收获的一份珍贵礼物。
这些信札,内容大体分为五个方面:
一是阐发对社会风气尤其是文坛现状的看法。田先生忧国爱民,勤于思索,每有见地,直抒胸臆。他几次针对当时文坛泛滥的不良现象,在信中写道:“现在纯文学的作品少之又少,作家和读者更多的关注是新的刺激,所以风气渐坏已成不争的事实,即使有些得鲁奖的作品也很少读者,可见如荷花之圣洁何其难也。”
二是告之他的活动情况和感受。先生早年曾在京津石穗等地搞过个人书展,影响很大。1994年在泉州帮女儿带小孩期间,当地慕名请求他开办一次个人书展。他信中告诉我说:“全国旅游交易会近日在泉州举行,几个政府官员正筹备我的《田人书法泉州展》,我将在此展示一下我的艺术,让闽南人感受一下北方的雄强和厚重。”先生有一次到甘肃开展传播张裕钊书法的讲学活动,回家后即写信告之讲学经过和收获,并将负重带回的两块洮河砚赠我一块,鼓励我习练书法。可惜我既无翰墨天分,又乏勤苦精神,真是愧对和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三是寄来作品征求意见。他的书法集《田人书风笔诀》《田野上人舞风颂》《八十抒怀》等长诗,正式书写出版前都给我寄过初稿。他学识深厚,文笔严谨,我自然提不出什么意见。但由此可见先生虚怀若谷的君子之风。2000年,田人先生写“古桃赋”一篇,附信寄我时坦诚地说:“寄上《古桃赋》,410字左右,有人说应先写桃花再写桃树,又说桃的部分写得太少。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而我则信笔为之。”使我更看到了先生的严肃认真和潇洒气度。
四是给我的习作助力加油。1999年,他听说我想出诗集,立即写信说:“这是好事,自古诗成胜得官,经济如有困难我可助一臂之力。”后来我又出过一本散文,他高兴地在信中说:“我识字不多的老伴过去喜欢听我讲聊斋,现在也说喜欢你这朴素土气的散文。”他看到我写的孙犁搞土改的系列文章,几次在信中说:“你能钩沉出这么多背景,是研究孙犁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有次还单独寄来一张设计精美的明信片,上书八个苍劲大字——常读大作,颇有荷香!
五是鞭策我努力读书。田人先生曾在一封信中说:“要想下笔有神,必须多读诗文。唐宋散文,颇多文采;唐人诗作,无人企及,你都要多看一些。”他是博览群书的人,每见报刊精彩美文,经常剪贴寄我,有两次看到事涉饶阳历史的诗词,还写成书法条幅寄来。为鼓励我读书,他还曾在信封中寄赠几枚菩提树叶,嘱我“作书签用”。这两枚柔韧透明薄如蝉翼的珍贵树叶,至今仍夹在我一本经常翻阅的唐诗选本之中。
2019年9月先生仙逝时我并不知情,因他的家人处理后事非常低调。事后他女儿用他的手机电告,我猛看熟识的号码,还以为先生又要和我倾心长谈,突闻噩耗竟一时哽咽无语。因之前一个多月老人还寄我一本他自书出版的四字长诗《衡水湖上》,签名时还认真写着准确时间“2019-7”的字样。谁知未见一面却突然天壤永隔了。那天我忍痛写了一篇悼文,题为《寄往天堂的信》,以慰他“素喜笔谈”的在天之灵。
现在轻抚这些陈旧斑驳的信笺,看着熟悉亲切的字迹,我常想,如果有什么纪念先生的活动,我将无偿捐赠这些信件。如果没有类似活动,我将复制珍存于档案部门。因为先生的书法和文字,肯定有其宝贵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含量。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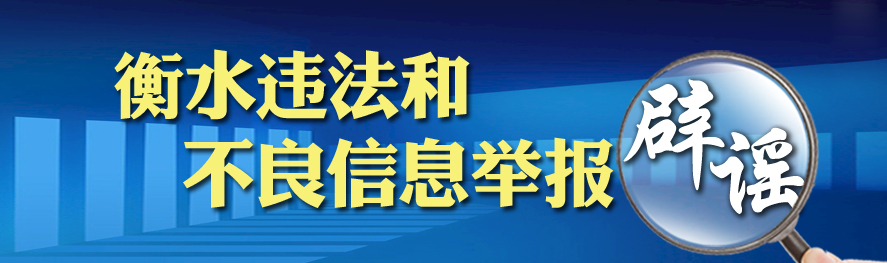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