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家乡人把煮鸡和熏鸡都叫烧鸡。明明是煮熟的,怎么却统称“烧”呢?
过去在电影里看过日本兵用刺刀挑着带毛鸡上火燎烤,也看过叫花子用泥巴包了鸡埋入炭火,那才算名副其实的“烧”吧。
记得小时候,乡亲们常说“山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人们堵着鸡窝捡几颗鸡蛋,却都不舍得吃,用来到供销社换成煤油咸盐,或在小贩手里换把小葱茴香,使寡淡的日子增添一点滋味和颜色。所以,鸡自然就成了庄户人的宝贝。尤其那些持家省细的老人,更把鸡看成命根子一样。“农村老太三件宝,闺女外甥老母鸡”。母鸡和闺女外甥划了等号,谁还会舍得去“烧”?
十来岁时,记得一次吃鸡肉,竟是从黄鼬嘴里夺来的。
那天半夜,突然听到鸡窝中的鸡“嘎嘎”惨叫,母亲惊呼一声:“黄鼬拉鸡!”迅即披衣下炕,顺手抄起灶边的烧火棍。没等她跑到鸡窝前,那只黄鼬正咬着鸡脖使劲往外拉。母亲急了眼,大吼一声,把烧火棍猛劲砸去。
黄鼬吓得松嘴窜逃,鸡却被咬断脖子,“扑楞”几下死了。
第二天母亲流着泪收拾死鸡。我以为要吃煮鸡了,她却说:“吃鸡肉丸子吧,还显着出数儿。”
鸡肉丸子不用油炸,而是像窝头那样蒸。母亲先剔掉鸡腿骨,又把所有细骨和肉一起剁成馅料,和上半盆秫面(高粱面),再掺点葱花盐末,然后揉搓成一个个黑红的面疙瘩上屉。因佐料太少,也没掺一滴油,所以出锅时虽弥漫着丝丝肉香,滋味却实在并不美妙。但这毕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生活“改善”,母亲就叫我给邻居们送去几个。我这才明白母亲说“出数儿”的原因。要是煮只整鸡,自家还不够吃,怎能匀给别人呢?我家对门是两个“成分高”的老人,据说年轻时过的是吃香喝辣的滋润日子,他们很高兴地尝了我送的丸子,感动地连说:“好吃,好吃!”
我却反感这种吃法。因不仅没尝几口肉,槽牙的龋齿洞还硌进一块骨渣,疼得我半天“吸吸溜溜”“嘶嘶哈哈”,就没好气地说:“以后做鸡,不会煮着吃吗?”母亲却答非所问地说:“以后堵鸡窝可千万要堵严!”
那时能吃烧鸡,在我看来实在是件奢侈事儿。
我的一个高小同学却多次吃过。他父亲在某工厂负些责任,人脉自然宽广许多。据说经常有人请他父亲喝酒,而烧鸡自然是拿得出手的佳肴。他说曾跟父亲赴过一次酒局,请客人见到他分外高兴,还没等开喝,就先拧一条鸡腿塞到他手里,并亲昵地拍拍他的脑袋说:“小子,尝尝大伯这条大腿!”同学几次谈起此事,总要哈哈笑着说:“这个大伯真有意思,竟把鸡腿说成自己的大腿!”
我自然有些少见多怪,就怯怯地问:“那骨头不硌牙?”他神气地说:“人家是德州扒鸡,骨头一嚼就烂!”
当时没吃过烧鸡的绝非我自己。
初中毕业那年中秋,我一个发小捡废铁卖了几毛钱,咬牙打回一瓶散酒,睌上约几个同伴找我同喝。我家只有半盆稀薄的剩菜,实在不足下酒。他又大胆到村边地里拔回几棵队上的花生,回来煮熟当做下酒之物。那次虽是平生首次沾酒,但我自觉并不尽兴,就嘟囔说:“要是有个烧鸡就好了。”玩伴却喝得舌根发硬,大声说:“过两年咱去当兵吧,万一熬成干部——挣了钱,咱们天天——买烧鸡!”
到了参军年龄,我们一起到五公村体检,在国营食堂吃了一顿焖饼,还见到了大锅炖煮的“烧鸡”。
五公烧鸡似有秘方,历史也长,几十年来仍然名声不减。那天我们等着吃饭,见院里架着一口出奇的大锅,里面煮着满满一锅鸡,沸滚的老汤“咕嘟咕嘟”冒泡。因为锅里太满难以盖上盖子,鼓鼓拥拥的鸡肉上竟平压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圆滚滚,油腻腻,就像一个光滑的大冬瓜。人们围着大锅,吸吸香气,心里都有点想入非非。但带队的民兵连长却并不舍得给人们买鸡,只是大声吆喝:“今天的炒饼管够!”吃完饭后,发小把我叫到一边,慢悠悠地说:“这一辈子,若脱生成那块石头就不冤了。”
他说话时,并没有笑。我点点头,也没笑。
何时开始吃到烧鸡,印象实在淡漠了。只记得儿子结婚时摆了几桌酒席待客,每桌上了一只烧鸡。但人们好像并无兴趣,有的甚至基本没动筷子,只得被几个养着爱犬的朋友带走了。
前年去一个农家乐饭店,上了一盘新菜“鸽子饼”,是把肉鸽连骨剁碎煎制的,颜色金黄,酥脆焦香。虽细嚼偶尔也有骨渣儿,但更令人食指大动。现在的人们,真是日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了。
看着美味的“鸽子饼”,我立即想到母亲做的鸡肉丸子,几乎落泪。母亲生前不喜欢肥肉,却爱吃烧鸡,所以我平时经常给她买。后来她的牙大部分掉光,很软的鸡肉也嚼不动,就只爱吃烧鸡的鸡皮。她常说鸡皮软乎,滋味大。所以只要吃鸡,我们全家就都把皮挑给她。
母亲去世三年了。生前我给她买过五公烧鸡和德州扒鸡,也买过北京烤鸭,但这种“鸽子饼”却是没买过的,因为这种吃食以前从没见过。但尝试“鸽子饼”做法的人,是否受到了鸡肉丸子的启示呢?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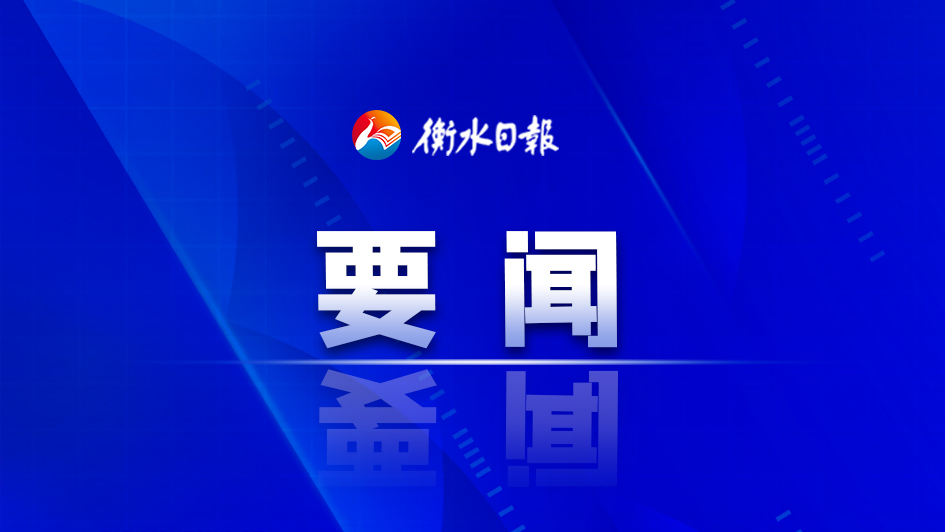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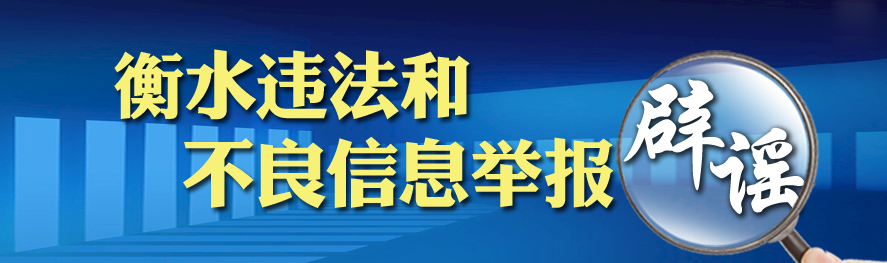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