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力宏婚变事件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王力宏前妻李靓蕾在控诉王力宏的长文中表达了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照顾三个孩子,料理整个家庭,全年无休的艰难。这点也引起很多全职妈妈的共鸣。
《中国妇女报》以“绝不应当是以‘爱’为名、滋长落后性别观念的陈腐温床”评王力宏婚变事件,指出了全职家庭主妇的绝望处境。对于这一议题,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曾进行过深度分析。安·奥克利认为,虽然职业领域的性别差异现象有所减少,但一种职业角色仍然完全是女性化的:家庭主妇。尽管没有法律禁止男人从事这项职业,但是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重重压力会让他们打消这种想法。女性等同于家庭主妇的观念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遍布其中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的根基。
不论是否有社会性工作,家庭主妇都是“除家庭佣工以外,负责大部分家庭职责(或监督家庭佣工来执行这些职责)的人”。安·奥克利采访了40位家庭主妇,她们都已婚已育,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其中有6个人不是全职妈妈。奥克利根据他们对家务、育儿、婚姻、就业和生活整体的满意度评估完成了《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这本书。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整理自这本书,较原文有删减和结构上的调整,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英] 安·奥克利著,汪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原作者 | [英] 安·奥克利
摘编 | 申婵
家庭主妇并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
当今思想中流行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对家务劳动的刻板观念。其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家庭主妇是被压迫的工人:她在每况愈下、令人不快且本质上是自我否定的工作中被奴役。另一种说法是,家务劳动保障了无止境的创造性和休闲性的人生追求。以这种观点来看,家务劳动不是工作,而是持家,而家是宝库。
关于成为家庭主妇最棒方面问题的回答中,我采访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指出自主性是家庭主妇最看重的特质。对“最糟糕”方面的问题的回答,虽未指明家务,但是都与婚姻、母亲身份和家庭生活有关。
但实际上家庭主妇的自由是从“某种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自由选择并进入某种生活的真正自由”。也就是说,她确实免受监督,但并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
自由是理论上的而非实际上的,“做自己的老板”意味着有完成家务劳动的责任。家务劳动是单方面的责任,不做家务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如一些女人列举的那样,这些不堪后果包括丈夫会愤怒和孩子会生病。
这就意味着,说家庭主妇有休闲时间是自欺欺人的。“做自己的老板”这一事实,其实是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做家务的心理压力,曾经是计算机程序员的乔安娜·吉尔斯说:
我认为最糟糕的是,正是因为你在家,所以你才必须去做这些事。即使我可以选择不这样做,我也并不会真的感到可以不去做,我总觉得自己应该要做。
因此,家务劳动是名义上广受赞誉的所谓自治性这枚硬币的另一面罢了。在对“最糟糕之处”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我采访过的妈妈们中,有28个人提到家务劳动的单调乏味,另有6人描述了女性要一直对家庭和孩子持久负责的负面感受。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家务劳动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
家务劳动被描述为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就像那句老口号喊的“女人的工作永远做不完”。有些人说做家务比有薪工作还要劳累,有些女性说做家务要付出的情感代价更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不像其他工作那样劳力费神。也有人提到家务劳动的非建设性,提到了单调乏味的劳动给主妇带来的情绪上的厌倦、沮丧,家务需要主妇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动作。而来来回回做,却换来永久失败的感觉。
当被问到“你认为家庭主妇和工作的丈夫一样努力还是不如丈夫努力?”时,一位嫁给办公室经理的前护士说:“更努力。你根本看不到他在工作——他不过是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其他人去干活。
一位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伊莱恩·考桑说:
我并不是嫁给了一套房子!我讨厌“家庭主妇”这个词……他们会问你“你是做什么的?”如果你回答说“我有孩子了。我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他们就会说,“哦,你只是个家庭主妇”。只是个家庭主妇!这可是世界上最艰辛的工作……你远不止是个家庭主妇……家庭主妇这个概念囊括了一切。
做家务不是单项的活动,它是各种各样任务的集合,这些任务需要各种技能与各种劳动参与。就像拖地与购买杂货完全是两码事;刨土豆、洗脏袜子和计划一个星期的食谱也是完全不同的任务。用相同的名称来称呼所有这些工作只会掩盖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将它们划归到同一指称下。实际上,有些家务活比别一些更讨人喜欢。有些家务活儿重复性更高,有些很累人,也有些更具有创造力等,不一而足。
毕竟,家庭主妇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做饭、洗衣、打扫房屋等——都可以独立地构成一份有偿性的工作。就像厨师的角色与商业洗衣店洗衣工的角色或者“家政服务”的工作者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以将家务劳动分为六项:清洁、购物、做饭、洗碗、洗衣和熨烫。在这六项任务中,熨烫是最不受欢迎的,我采访的3/4主妇都持这种消极态度。接下来按不喜欢的程度排列,依次是洗碗,清洁、打扫房屋和洗衣服。它们和熨烫一样都涉及一系列的重复动作,这些反复的动作类似工厂中的流水线工人,与无休止的重复性工作捆绑在一起。
烹饪被认为是最有趣的活动。它是一项挑战,也可以是一门艺术。毫无疑问,这种对做饭具有创造潜力的看法,受到了广告以及女性杂志与类似文学作品的影响。对做饭任务的详细展示,旨在将其从“工作”维度中拉开,并将其置于有创意和富有愉悦性的维度中。
可是尽管人们说做饭极具创造力,但是实际操作呢?时间(和金钱)的有限,阻碍了享受烹饪的乐趣。要知道家庭主妇不仅是位大厨,她还同时是洗碗机、清洁工、保姆和照看孩子的人。丈夫们要求在特定时间用餐,小孩子肚子饿时就会大哭,那些本来能够花在做饭上的时间还要用来拖地或换洗床上用品。“思考吃什么”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无论这个任务实际上多么具有创造性。
这些家务图景与通常认为的家庭主妇是闲赋阶层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人们不能指责家庭主妇“整日无所事事”,同样也没有合理证据来说明她们唯一的“工作”是“富于创造性”的。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家务劳动把家庭主妇的时间撕成碎片
家务劳动是如此碎片化的工作,无论做家务需要什么技能,全神贯注都不是必需的,而且要完成许多不同的家务的结果是,它会使家庭主妇的注意力分散到许多不同的方面。孩子实际上会放大这种碎片化效应。他们使人不能全神贯注,这常常也是家务活动中断的原因。做家务时不时想到孩子的程度不仅反映了家务零碎化的特质,它还标志着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结合在一起的困难。
像碎片化一样,家务劳动也带给女性强烈的时间压力,她们会表示要做的事情太多。例如朱丽叶·沃伦所说:
自从我有了孩子以来,我做家务的水准直线下降了。我想这是因为我不能不间断地做任何事情,对此我仍不习惯。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我非常清楚,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过去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但现在有些事情我没有时间可做。我可能会在每天开始时有很多计划,但最后我实在太疲倦了,于是计划都泡汤了。令我心烦的是,明天又是这样……
由于无法控制的因素而造成的时间限制,每个任务都无法获得她原本想要给予它们的时间和关注。与许多工作不同的是,家务劳动通常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不会感觉根本没有做。然而忽略或最小化某项家务充其量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家庭主妇意识到这一点后,又会比她们在其他类型的工作中感到更为强烈的时间压力。
家庭主妇也体验着某种程度的孤独,仅仅是因为家务活儿是在家里完成的,家庭主妇唯一忠实的陪伴者是她的孩子。因此,与成年人建立令人满意的社交关系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对于某些女性而言,白天与一些其他人的社交联系流于表面,试图在提醒家庭主妇,她缺乏的那些深入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是多么重要。
家庭主妇的工作时间在当代社会中几乎是最长的,在做家务时,他们也要对孩子负责,必须知道孩子在做什么,而在照顾孩子时,她们又几乎总在做家务活。例如,更换婴儿的尿布或洗尿布;喂孩子这项活动则包括(最终)整理妥当、收拾清洁和洗碗。
从育儿的角度来看,无论家庭主妇身在哪里,她照顾孩子的责任一直如影随形。当孩子入睡时,她对孩子的责任依然如故,如果孩子突然醒来并需要她的关心照顾,她就必须做好准备马上中断她手头上正在做的任何事。
家庭主妇的工作没有薪水。因此,必须要有其他的隐性奖励。丈夫对家庭主妇来说是一个潜在的赞许人,但他能否有效地扮演这个角色?在我采访的40名女性中,没有人自发地提到,丈夫的评价是她们做家务所获得的一项私人奖励,有8名女性说,她们的丈夫从未对做家务这一事情发表评论。
对于确实得到丈夫赞赏的那些家庭主妇来说,得到积极的评价通常是有条件的。因此,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得到过改善,女性更多的是提及挫败感。
有时,当他带某人回家时,他会说:“今天家里看起来真不错。”但是别的时候,他从来没这么说过。(长途副驾驶员的妻子)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养育孩子让家务劳动变得更辛苦
家务劳动作为一份工作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与另一项工作结合在一起:养育孩子。大多数家庭主妇有孩子,实际上,几乎所有母亲都是家庭主妇。孩子是造成家庭主妇作为家务劳动者的挫败感的主要根源——她的工作因需要不停地照看孩子而被中断。
育儿与家务的组合实际上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矛盾并不仅仅在于孩子是不能处理的生物个体,他们使整洁的房子变得乱糟糟,并要求主妇在做饭或打扫房间的同时把他们喂饱或陪他们玩耍。原则上,这两个角色在根本上是对立的。
服务性的功能是家务劳动的基础,而孩子是人。育儿则是“富有成效的”,不像家务劳动是没有收获的。家务劳动具有短期和重复的目标,即今天打扫了房子,明天还要再打扫,以此类推,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皆复如此。母亲的角色只有一个长期目标,也可以被描绘成母亲自己最终的失业。一个“成功的”母亲会将孩子抚养长大,并让孩子在没有母亲的帮助下能独立行事。
许多中产阶层女性育儿的态度是对母亲和家庭主妇这两个角色进行清晰的区分,而工人阶层对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无差别对待的主要后果是,着急强调了母亲角色的服务性方面,这时育儿和家务便成了同义词。这种同义,意味着她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清洁和整洁,同时强调了消费主义。
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也缺乏此种区分,家庭主妇即指女人、妻子和母亲,人们很少单独论及其中的单个身份。社会对一个在家照看孩子的女性的职业描述不是母亲而是家庭主妇。
中产阶层家庭主女妇朱丽叶·沃伦描述了进行这种区分时的实际困难:
我曾经读过所有有关有了孩子后的文献,而且发现文献中确实有一种极大的享受光环——没有人告诉你你辛苦的部分——一直照顾孩子的经历是多么令人沮丧,一周七天皆是如此……
正如朱丽叶·沃伦所观察到的那样,完成家务劳动并专注于有回报的抚养子女方面可能会需要很多精力。可能这个孩子被人称为“超棒”或“漂亮”,但是他也是家庭主妇内部情绪混乱的原因,这种混乱程度只能与她找不到足够(不间断地)时间打扫房屋的外部混乱相比拟。另一个原因是母亲身份的“神话”特性,它从产前阅读中逐渐被女性所吸收,它与主妇的实际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母亲身份有它自身的回报,但这一身份也剥夺了相当多的东西,而这一面在我们的社会中,被母性角色的荣耀光环所掩盖。
在对育儿“满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孩子的矛盾情绪和对母亲角色的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个问题的一个类似问题,是育儿方面的询问——“你喜欢照顾孩子吗?”就措辞上而言,这个问题很难说很传统:它允许回答都给出否定的答案,但另一方面社会语境只能包容那些给出肯定回答的人。
实际上,我采访的40名女性中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喜欢”这种否定答案。缺乏否定回复可能也是一种标志,它表明人们对母子关系持消极态度在社会上是不能被接受的。面对要认同母亲角色的强大压力,对育儿活动的不满表达可能会被主妇认为是自我威胁。母亲的社会形象赋予了母子关系一种充满母性光辉的相互满足感,女性带着自己也会喜欢照顾孩子这种期望长大。成年女性角色和母亲角色之间的等同,排除了人们会公开拒绝孩子和公开推卸养育孩子任务的可能性。
育儿工作与家庭主妇的角色需求相竞争意味着,对于作为家务劳动者的母亲而言,孩子有时候会被视为获取家务工作满意度的障碍,对于孩子而言,将他们的需求与家务的需求并置,只会让他们体验到失望和沮丧。
男人可以通过参与育儿工作来缓解这一困难,但是从女性角度来看,这种趋势可能是一种恶化和倒退。男人喜欢的育儿活动,一般是与孩子们玩耍,带他们外出和哄孩子上床睡觉等。很显然,他们对抚育孩子的另一面:如工作般、例行常规、不太愉快等,强烈反感。父亲角色的此种扩大对于女性来说是个不幸的改变,因为她们从中得不到半点好处,除了暂时有点空闲可以去做家务活(例如,“他每天晚上和孩子们玩耍,所以我可以洗好碗”)。与此同时,她们还失去了一些父母陪同育儿的情感回报。对家务的满意度可能是有所提高,但这是以牺牲养育孩子的满意度为代价的。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男人们干什么去了?
现代婚姻中关于夫妻平等的观点不仅仅是关乎态度上的平等,更关乎使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行为变化。例如,如果丈夫实际上没有与妻子平等地分担家务,那么发生的一切就是,除了传统的家庭角色,女性还要兼顾新获得的工作角色——从业者。在我的研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丈夫正以“平等”一词所暗示的参与程度投入家庭生活。婚姻中的劳动分工模式与其他领域之间缺乏一致性,这表明实质上有很大一部分的家庭压迫被隐藏在所谓“平等关系”的婚姻关系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通过工作或职业在男性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来进行解释。
我采访的40名女性中大多数人提到了家庭不平等的另一个根源,即使男人有个人偏好想更高程度地参与家庭事务,也可能会因为坚信“丈夫的位置不在家中”这种观念而不能真正实现其目标。同样,女性可能主观上想少做点家务事,但她必须面对认为女性“属于”家务和育儿领域的社会规范的压力。
家庭主妇对丈夫不参与家庭生活的愤懑是很普遍的,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偏家庭化的丈夫是很受褒扬的。男人在家务方面提供帮助的重要性也影响到女性对丈夫在育儿方面表现的感受。作为一个母亲同时又是家庭主妇的女性,在缺乏家务援手的情况下,很难享受到育儿的乐趣:孩子变成了家庭主妇身份裹挟下的母亲角色的一个失败感来源。有意愿做家务的丈夫减轻了女性的家庭负担,并为她们采取更加放松的方式来进行育儿工作铺平了道路。
然而,很少的婚姻里,丈夫会特别地倾向家庭化,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也仍然存在着基本的家务劳动分工: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仍是女人的主要责任。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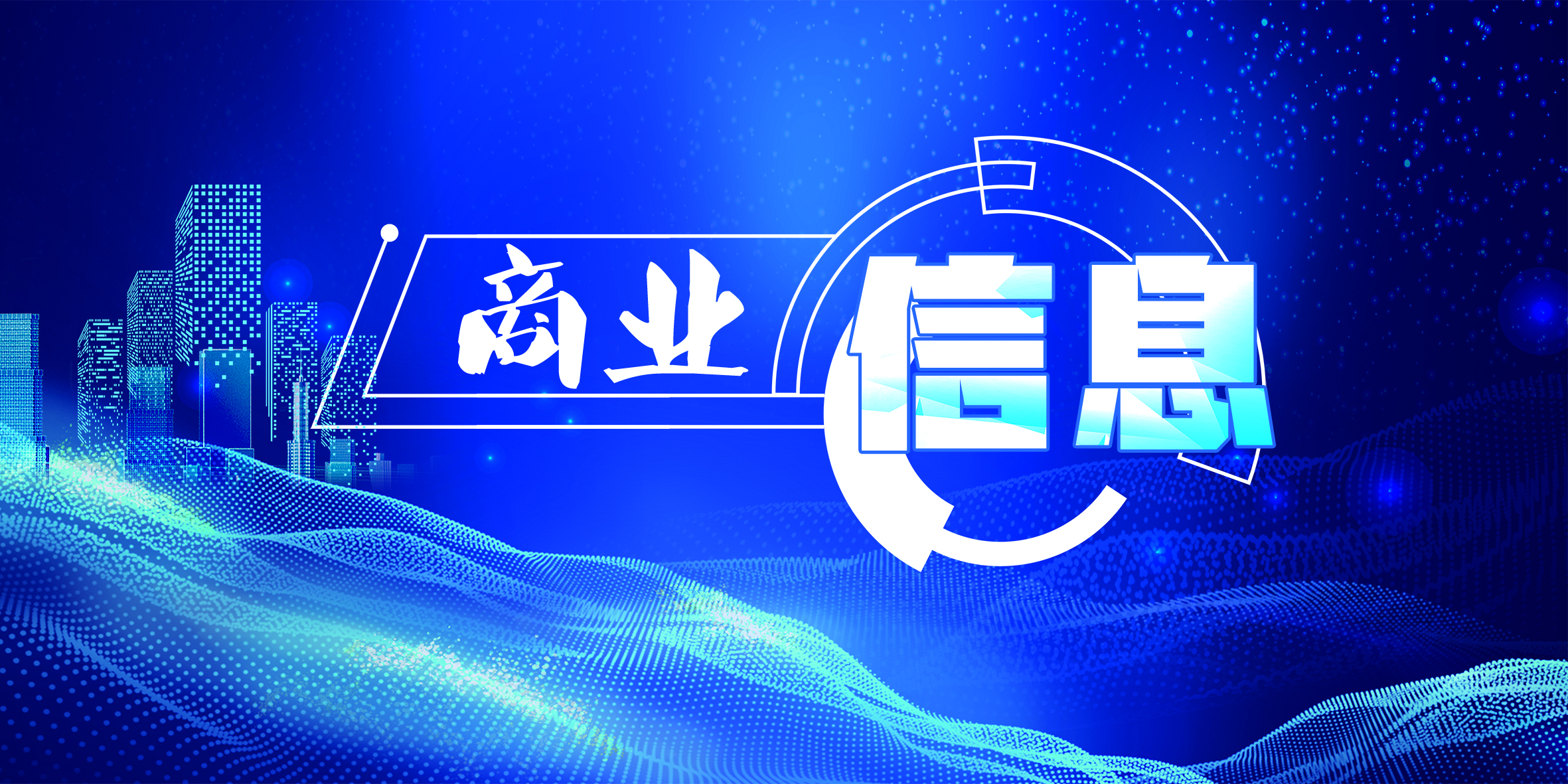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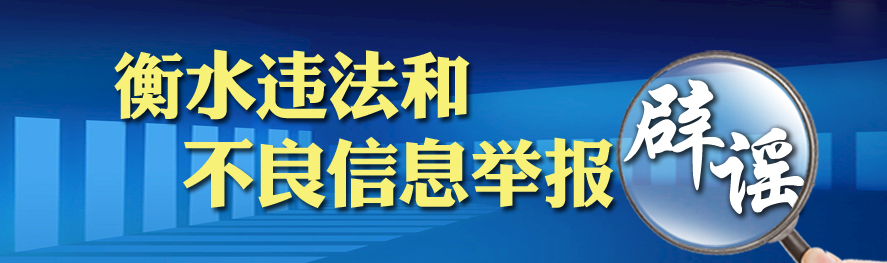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