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爷和七奶老两口吃晚饭的时候,拴在院子里的大黑狗伴着大门咚咚的响声狂叫起来。
说是晚饭,其实还不到下午六点。六点以前必须要吃完晚饭,这是儿子和女儿下的死命令。孩子们小时候要听爹娘的,爹娘老了,反过来要听儿女的了。况且胃不安,则卧不宁。
夏天的五点多,正是庄户人避了炎炎烈日,下地干活的时候。
小饭桌放在院中心那棵十几米高而又粗壮的侧柏树下,微风像一把小提琴,让柏树叶子如痴如醉。这棵柏树是七爷和七奶结婚那年,七奶在辽宁葫芦岛当兵的哥哥从东北弄来,当嫁妆送给妹妹的。那时候柏树在华北平原这一带是个稀罕树种。
今天晚上老两口吃饭的气氛有些不正常。七奶说“五嫂怕是熬不过今儿去了。”七爷“嗯”了一声,饭菜在没牙的嘴里发出了吧唧吧唧的声音。“我就知道是回光返照,昨儿下午,我去她家,五嫂还底气十足呢,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这些年照顾了她们娘俩,还说只要有我活着,她儿穗子就有人管。”
穗子从娘胎里出来就残疾,少一只腿,人们都拿他当怪物看。从小死了爹的穗子却把七爷当爹看。
五嫂还给你撂下什么话没有?七奶的话有些咄咄逼人。
七爷顿时紧张起来,他停止咀嚼,吞吞吐吐地说,五嫂说她头死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口柏木棺材,因为她活着时,从来没住过多么漂亮的房子。
所以,你就答应她了?刚才穗子说,我还不信呢,我说那是孩子们打算我们百年以后,给我们做柏木棺材的。
七爷带着无可奈何的口气说,我能忍心去拒绝一个快入土的人吗?
七奶说:“我不管,你怎么拉出去的屎,你就怎么给我收回去!你以为你还像当村支书那会儿,拿我当傻瓜使。再说,这些年,要不是你在村里第一个给她们娘儿俩办了低保,她们的日子还不知道过成什么奶奶样呢,她倒好,临死讨起人嫌,竟打起咱家柏树的主意来。”
七爷被七奶噎得说不出话来。在云上村当了三十五年的支书,七奶和一双儿女帮着他在村里当了三十五年的“奴隶”。两年前,也就是七爷六十九岁那年,感到力不从心的他才卸了支书的担子。本来他想好好补偿补偿她们娘几个,无奈,儿女们早成了家,况且儿子都当了爷爷。现在只有老伴成了他心中的宝。正在七爷为难的时候,大黑狗的狂叫和大门的咚咚声给他解了围。
七爷喝住黑狗,打开大门的那一刻,一下子像泥雕一样站在那里。他吃惊,已经二十多年没跟他犯话的亲二弟,带着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表情站在他的面前。
弟兄两个谁都没有忘记,二十多年前,他们来自同一根脐带流出来的血。
七爷刚当村支书那会儿,云上村还是一个土地贫瘠的村庄。盐碱地,土沙坡,蛤蟆尿尿就趴窝(意思是蛤蟆的尿就能把房子冲倒)。
七爷当时年轻气盛,他发誓,以后如果云上村有一个人饿肚子,他就跪着走路。
当时的七爷绝不是吹牛皮。他看了好多书,知道治碱固沙就要栽树。于是他带村民们栽了很多种树。六年后的一个冬天,一些小树已经长成大树的时候,七爷忽然发现,树林里丢了八棵大树。夜里十二点多,七爷顶着刀子一样的北风去捉贼。当他看见村外路边上停了辆拖拉机,二弟和他的小舅子在用锯子锯一棵大槐树,因为二弟的小舅子准备盖房子用木料。
七爷怒了,他要带他们到乡里去自首,二弟和他小舅子却把七爷狠狠揍了一顿(当然没有打到要命的部位)二弟的小舅子最后撂下狠话,如果报官,他就敢杀他全家。
果然,七爷第二天没有报官,他并不是因为二弟的小舅子的恐吓,而是七爷的爹娘拼了命保二弟,爹娘要死给他看。不处理二弟,七爷就没法给村民们一个交代。于是他就拖着被二弟他们打伤的双腿,让二弟扛了一根木头,陪着他冒着严寒在村里游了一天的街。然后二弟又交了罚款。
这些年二弟的儿子出息了,在城里搞了建筑公司,一家人都搬城里去了,两家就更互不往来了。
这时,二弟首先打破了僵局。他脸上带着愧疚喊了声大嫂,“大嫂,弟弟今天给你赔理来了”,七奶一下子高兴成了菊花脸。“赔什么理啊,你心里有你哥嫂,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不知二弟今天为什么回来?”七奶搬了把椅子,又给二弟拿了瓶矿泉水。
二弟说他在村里的微信群上看到五嫂病得厉害,他回来看看五嫂,五嫂对他有恩。“当年我偷树,就是五嫂给咱爹娘出的主意,才让哥没报成官。”说到这里三个人都笑起来。七爷说“怪不得你这些年没少帮五嫂娘儿两个。”二弟叹了口气“我来晚了,五嫂已经不省人事了。听穗子说,她娘就喜欢你家的柏树做棺材。我说穗子,你娘喜欢柏木棺材,叔花多少钱都给买,你大叔叔家的柏树动不得,那树是我大哥大嫂的命。”二弟的话似乎伤了七奶的自尊心。她有些气急地说,“二弟,谁说我们舍不得了,你大哥早答应穗子了。再说我们老两口百年时,一火化,装个最好看的骨灰盒。”七爷和二弟都笑了,忽然一只金翅雀在柏树上叫起来!
作者:任秀红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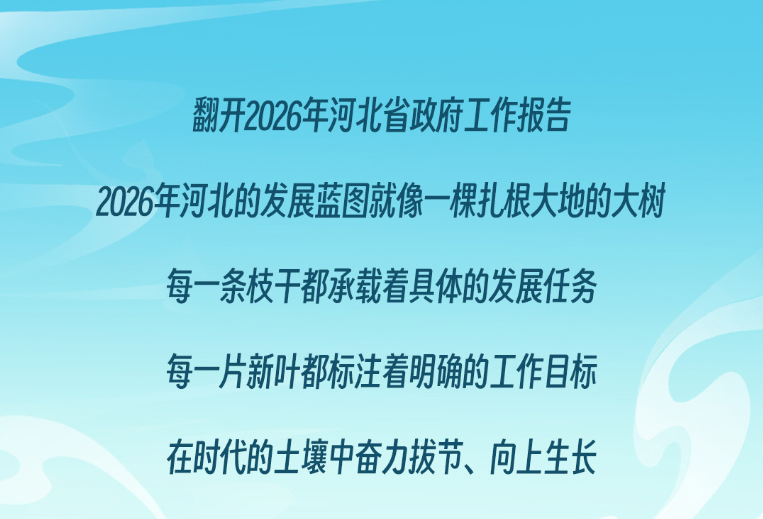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