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的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也在光绪元年七月过世,吴汝纶除服后复入李鸿章幕府。光绪五年九月至六年二月,受李鸿章推荐,吴汝纶署理天津知府。光绪七年闰七月,补冀州直隶州知州,初十接印视事。
吴汝纶担任冀州知州后,决意改变百姓生活,造福于民。

吴公河水闸 陈康 摄
光绪八年,为冀州各县缺水事宜,吴汝纶先派胞弟吴汝绳到磁州联系知州张受之,实地考察踏勘滏水、漳水,又上书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在磁州老君庙建闸,引漳水入滏水。光绪九年直隶南部发生三十年未有的大水灾,引漳入滏之事自然中断。吴汝纶在好友李传黻的信中说:“水围城郭,数月不消。缘自州北至衡水地势迂下,现因衡水民埝决口倒灌,数十里汇为巨浸,皆古时葛荣陂故地也,今则庐舍田墓灿若列星,水之吞噬,无复干土。州之西境,则新河民埝亦决,溺漫四野,被灾百余村”。吴汝纶决定恢复李秉衡未竟之事,开渠引冀州本境及衡水县南积水入滏阳河。

滏阳河与吴公河交汇点 陈康 摄
前任知州“北直第一廉吏”李秉衡就有循旧河修渠以通滏阳河的动意。乾隆时方观承“发帑兴修”滏阳河闸,嘉庆时闸坏河淤,李秉衡“用官牛资本京钱八百串,用民工千人,挑挖七八日”(吴汝纶《与朱敏斋太守》函),后因经费难筹,半途而废。李秉衡卸任时推荐李馥堂、张廷湘给吴汝纶协助办理州务。当时李馥堂已经七八十岁,吴汝纶倚重张廷湘,决心开渠,他首先争取李鸿章的支持,得到了部分的经费。张廷湘当时四十多岁,正值壮年,随后率“深州贺嘉枏墨侪、衡水马景麟仁趾、州人张增豔雪香、刘步瀛旋吉、李喆生鉴波”等开始“度地量工,赋丈授役凡十余月”,开自冀州城西的尉迟潭,到冀州城南九龙口入城东海子,贯穿海子东部至滏阳河建闸,闸高二丈六尺,即今老龙闸,成“六十里之渠”,“明年濬而深之,又明年广之,凡用金十万”,而“冀东衡南之田,变瘠为饶者十余万亩”(《张楚航先生墓碑》)。

滏阳河与吴公河交汇点 陈康 摄
贺涛作《冀州开渠记》云“水即有归,田皆沃饶”。吴汝纶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也不无自豪,“所开新河旁,赤卤大半变腴,穷民各就近处垦种。共二十余顷”。光绪十一年七月五日吴汝纶对好友潘青照说“河工徼幸粗成,一昨居然有津郡货船来泊西关,殊以为喜”,天津货船能够驶入冀州西关,吴汝纶高兴异常,开渠引水成功后,舟楫往来,对推动冀州各属经济发展极为有利。
为了给百姓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吴汝纶大力整顿治安,处理政事。吴汝纶向李鸿章汇报工作说,到任后“以听断为主,每月结正讼狱约在四五十起,庶冀穷民少清讼累,不为胥役所鱼肉”,同时他正在“清查盗源”,推行联庄之法,“督令各村办理联庄,搜访正人为之分任,略师保甲之意,而去其无益烦琐之事”。
吴汝纶到任后第三个年头,光绪十年年初,冀州判署竟然在城内被盗,吴汝纶大为恼火,私费三四千两银子,调来名捕刘永胜、任国安父子缉捕。同时他招抚冀州本境雷三群、李振邦等盗,为其所用。
吴汝纶独子吴闿生说其“善御下,有剧盗名闻远近,前政不能制,归命先君,尝得其死力,以此捕治盗贼,无不效者”。吴闿生作《雷中正传》说,前任知州李秉衡以捕盗称,围捕雷三群数次,不能缉获。吴汝纶任冀州三年,雷三群为其德政所折服,吴汝纶招雷三群入署,待之甚厚,为改名雷中正,甚得其力。吴汝纶离任时,雷中正送至州境,洒泪而别。袁世凯督直时,亲访吴闿生,欲起用雷中正出为捕盗,但雷已逝世。
经过吴汝纶大力整治,光绪十三年腊月初四在给李鸿章的总文案景翰卿信中说“州境托庇粗平,监狱近已空无一人,殆数十年来未见之事”。民国《冀县志》载,通过推行联庄之法,在州境数十里内,“击柝相闻,呼声相应”,“士农工商咸得安居乐业”。
吴汝纶在冀州更为突出的贡献是兴办教育。
吴汝纶任冀州知州以文教兴政务,政教一体。吴汝纶到任冀州第二年开始,苦心经营信都书院。据民国《冀县志》记载,在光绪八年“知州吴汝纶筹银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两,钱一万九千二百三十缗,置地九百二十亩,延名师,备膏火,时新城王树枏、武强贺涛相继为山长,萃一州五县高材弟子,课以经史词章有用之学,连岁登甲乙榜者数十人,而州人赵衡、李谐韺等尤以诗古文词蜚声于世。论者谓书院人才,最为一时之盛”。
吴汝纶对包括书院在内的教育革新有重大贡献。吴汝纶召集老成宿望,在家里居不仕的学者到冀州信都书院内任事,得十几人轮流出任董事。又变更书院旧章,为省往返劳顿,定为每月初二官课,初三斋课,连日并考,到考期这十几人都来到书院,共同论学议事。为信都书院首创监院制,即“选其文行优长者,使监院。监各学生出入几所业勤惰。”确保办院效果。时任信都书院监院有:北方撰文有名的赵衡、以诗词著称的李谐韺等。
吴汝纶在给弟子黄凤翙撰写的墓表中说:“自是月一会书院,是时余所得州士并来庭,数之已十许人,凡有施为,便不便,兴革于民。必与此十许人,其视一州之事,皆若家事然。先是则商较利病,事及则均劳逸,忍谤怨,争难趋险,竞智献力,不稍观顾畏避瑟缩”。贺涛作《尚君采章六十六岁寿序》时略述当时盛况,月考之期“略尊卑之分,泯主客之迹,黜彼我之见,翕然欢然,不知其孰为官,孰为士,孰为宾师也,而生徒执业其中者,亦相与维系如一家,各以所闻见传播乡里,故其时冀属多善政,习俗为之一变”。吴汝纶以纯朴学风所体现出的个人魅力来推动地方政务,易宾主为师徒,变官绅为师友,变师生为家人子弟,由是政通人和,诸如开渠种树、保甲均徭等善政均得以施行。
民国时张庆开集合在京读书的冀县籍一百多学生合影,并编辑一通讯录,请赵衡作《冀县学生同学录序》一文,赵衡在序中说:“维冀州地故辟左,士子读书能以学问发名于时,数百年来不数数觏也。自桐城吴先生来为州,不鄙夷吾人,兴学造士,为广置书册,先后延新城王晋卿先生、武强贺松坡先生都信都书院讲席,咨使问学,又亲与为师弟子,口传身授,诲我循循。不数年风俗丕变。上焉者于问学之途,具得门径;其次亦能猎取科名。番禺李侍郎提督顺天学政,试已归京,语人‘畿辅文风,冀州第一,天津次之,大兴宛平不足数也’。变法后天津严范孙侍郎为直隶提学司,每与吾州人燕语,辄谓‘畿辅学务当以冀州为中心点’,‘中心点’者,日本人名机要之言,侍郎尝游日本,故称引之。当是时庆开尊甫楚航先生为荐绅,吴先生倚办如左右手,先生亦引为己任,一不以委人。迨吴先生去,先生守其法,历艰虞不变,垂二十年。人才辈出,文章丕焕,迥非他州县所能跂及。今吴先生之学稍稍衰歇,往书院所收书册亦多散失,然人尚知学,所学亦具本末,与他州县有所劫于外而中无主者自不同,而所在城市最,此间学者之数即有百数十人之多,不可谓非盛也,此吴先生之余烈也”。
吴汝纶兴学“余烈”,岂止冀州本境,其五属县,连及赵衡教学七年之深州,甚而故城、景州等地,其弟子、再传弟子无数,流风所及,今日衡水地区基础教育高于一省,不为无因。
光绪十四年六月,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张裕钊转任江汉书院,李鸿章欲安置其女婿张佩纶主持莲池书院,当时舆论大哗,莲池书院师生有退院之议,李鸿章踌躇乏策。十月初吴汝纶至天津拜见李鸿章,请辞去冀州知州,主讲莲池。十五年二月,吴汝纶卸冀州任,举家迁至保定,至光绪二十七年。吴汝纶任莲池书院最后一任院长,而且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院长。
自此吴汝纶终其一生,锐意讲学,积极探求西学,主张新学旧学并重,为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田卫冰 编辑:贾亚楠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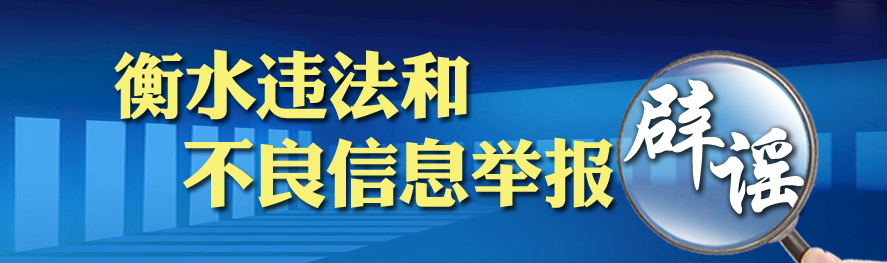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