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
《小团圆》的出版颇费周折。
宋淇夫妇去世之后,他们的儿子宋以朗先生便继承了张爱玲作品在港台的版权。他写的整篇序言也基本在说《小团圆》出版的合情合理合法。1992年2月25日张爱玲在给宋淇夫妇的信中最后一次提到《小团圆》:“还有钱剩下的话,我想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有出版的出版……(《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
宋淇夫妇没有同意即时出版《小团圆》,完全是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他们担心时在台湾的胡兰成借此自我炒作,给张爱玲带去新的纠缠与困扰。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主要集中在邵之雍这个人物的设定与结局上,不想借给胡兰成一架青云梯。张爱玲在当时接受了这份好意,但不知为何直到最后,都没有完成修改(她可能根本没有动笔修改)。
宋以朗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胡兰成早已过世,那一份担心可以视为不存在了。”他从更多的信件中分析,张爱玲说要销毁《小团圆》既不是她的本意,也不是她最后拿定的主意,所以《小团圆》可以出版,不必像卡夫卡那样被视为“背叛的遗嘱”。
《小团圆》怎么可以跟《变形记》攀比呢?在张爱玲的全部作品中,《小团圆》最多算一篇中下乘之作。自从张爱玲移居美国,她的创作才能几近枯竭,除了修改和翻译自己的作品,她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小说。《小团圆》她也是写写停停,近于难产,这样就知道她封笔之作的质量了。
伤痕文学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写道:“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1978年初,大一新生卢新华将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一时间,这篇小说在复旦校园迅速传抄。《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16条修改意见。8月11日,刊登小说的《文汇报》一日加印至150万份。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在当代文学史上,这便是“伤痕文学”的肇始。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这也印证了季老对“伤痕文学”的看法。
招生
1978年8月,陕西第八棉纺织厂革委会收到北影致函:(一)学院经过看张艺谋作品和面谈,为了让他有深造的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破格录取;(二)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张艺谋已经工作满五年,所以上学期间请原单位照发工资。并请厂里给张艺谋作一个政审,由张本人带回。
那一年,张艺谋曾下乡做了三年农民,又在棉纺织厂当了七年搬运工,28岁的年纪已经超出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六岁。年龄是死规定,人人爱莫能助。文化部长黄镇爱惜人才,有了他的过问,事情才出现如上转机。
2004年,清华美院博士生导师陈丹青辞职。在辞职报告中说:“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他不认同的一点正是:不少考生因为外语和政治两门成绩不合格,而与艺术学院失之交臂。
与我当年考研外语不及格相比,张艺谋是多么幸运。
士
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士钊与鲁迅分属于“文言”和“白话”两个阵营,其间有一小段关于“士”的争辩。
1923年,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文中借“二桃杀三士”典故,讽刺白话文之不可取。“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鲁迅当即撰文指明,“二桃杀三士”典出《晏子春秋》,是晏子设计用二个桃子杀了三个武士。“三士”非为“三个读书人”。他借机讽刺:“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1925年9月,章在《甲寅》周刊上重发《评新文化运动》一文。按语中写道:“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鲁迅毫不示弱,亦将原批评文章于《莽原》半月刊重新发表。
其实“士”在春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介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的最底层。在文化上,士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术等多种教育。既是读书人,也可充任武士。雷海宗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有解:“当时的人可以说没有文武的分别。士族子弟自幼都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士是文武兼备之人,有健全的人格,有自己的信仰,视荣誉为生命。雷海宗先生说,战国之后,这种文武兼备全面发展的“士”基本上绝迹了。
基于此说,有人讲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汪先生也未必认可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今天》
北岛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写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这篇文章写在《今天》被查禁的第三十年。由北岛、芒克创建的这份民间刊物只生存了十八个月,出版了九期双月刊和七部系列出版品。相信现在的年轻人早已是闻所未闻了。
评论界将发表在《今天》上的诗统称为“朦胧诗”。可是北岛却不怎么认可这顶帽子。
读李辉编著的《黄永玉的文学行当》一书得知,《今天》创刊号以“动物篇”选发一组“动物短句”,作者署名“咏喻”。
北岛有《回答》一诗。开篇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有诗《一代人》。全诗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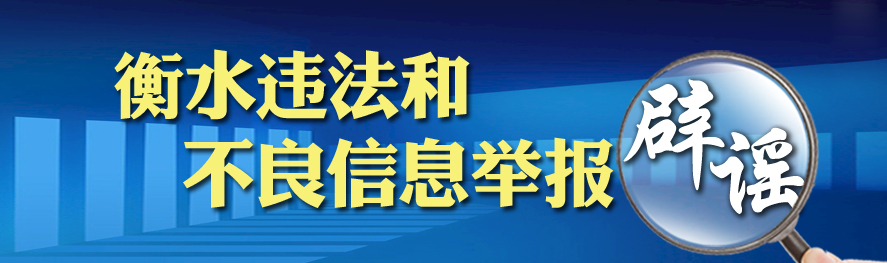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