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
1922年春夏之交,梁实秋与周作人关于诗歌创作中“美丑”理念问题发生争辩时,他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恰好清华文学社有意邀请周作人来校演讲,他们一致推举由梁亲自出马去北平西城八道湾。梁实秋本想拒辞,但又认为争论归争论,并无其他干涉,见见也无妨。
多年之后,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回忆:“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翛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
此等文人相交的风气怕是早已绝迹了吧。
喇叭裤
1978年,喇叭裤从广东登陆,像一股飓风迅速席卷内地各大城市。在易中天读书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校方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其时,喇叭裤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象征,穿喇叭裤既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看到“问题青年”遍布校园,校方自然拉响了警报。
很快,标语下方有学生写了一句诘问:“请问,什么裤能吹响?”路透社惊呼: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20多年后,易中天在某大学演讲特别提到,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早穿喇叭裤的地方——广东。
大约十年,喇叭裤才从南方都市走到了我们北方小小县城。一时间,县城里男孩儿女孩儿趋之若鹜,人人脚下拖着两只肥硕的喇叭筒。我们的老师视之如猛虎,纷纷拿起剪刀守在学校门口。即便如此,最后也没能阻挡喇叭裤占领校园。
公案
康熙朝的一桩公案。三个人,三种人性。
康熙十二年,耿精忠在福建造反。此时李光地和陈梦雷恰好都在老家告假,成为事实上的附逆之人。李、陈二人既是福建同乡,又是同科进士,情义笃厚,朝野皆知。于是二人密约上“蜡丸书”给朝廷,告知耿精忠谋反的详细情况。二人商量完所有细节,决定由李光地起草上书。此等生死攸关之际,没想到李光地夺情卖友,“蜡丸书”上独自具名落款。平叛之后,李光地扶摇直上,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而陈梦雷因附逆罪臣,逮捕下狱,贬戍奉天。陈梦雷满腔愤恨,屡屡上告,做起了康熙一朝的上访钉子户。多年之后,康熙知道了事情原委,在一次巡视关外时,他决定召见陈梦雷。
陈梦雷以为自己沉冤昭雪的日子终于到了!想不到康熙皇帝并不关心他的冤屈,只一味挑唆他告发李光地的不忠之处。面对康熙的暗示与胁迫,陈梦雷只说:“李某负奴才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奴才怎敢妄说?”康熙既不为陈梦雷的纯厚感动,也不为李光地的忠诚欣慰。他对这个回答极度失望,极度气愤,怒斥道:“你是个罪人,如何见得朕?你今日有话不说,自此后终无见朕之日矣!”此时,陈梦雷才明白,皇上是想整治李光地,借人之口,找些把柄,免得自己落下暴君的口实。
康熙之狡诈,李光地之阴险,陈梦雷之坦荡君子,俱可观矣。
女先生
李洁《1912—1928:文武北洋》书中透露:鲁迅冒着砸碎饭碗的风险参与“女师大风潮”,其实主要是因为“二许”的缘故。所谓“二许”,一指鲁迅同乡好友、前女师大校长许寿裳;二指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后来成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此事谨为一记。不置一词。
不过,我们还可以更多些地认识一下“女师大风潮”中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先生。杨荫榆,188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书香门第。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1925年因“女师大风潮”而于8月去职。后来杨荫榆回到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兼授外语,1935年创办二乐女子学社并任社长。1937年苏州沦陷后,杨荫榆目睹日军种种暴行,多次向日军长官抗议,后被日寇残忍枪杀。
我们这一代人,但凡知道杨荫榆这个名字,大都是读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她的身上贴着诸多标签——镇压学生运动的学阀、北洋军阀的帮凶、广有羽翼的校长、面目狰狞的卫道婆……其实辞职之后,杨荫榆回到苏州,住在二哥杨荫杭(杨绛父亲)家中,过起了与世无争的教书生活。转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杨德群等47人被北洋政府枪杀,客观来讲真得与杨荫榆先生甚不相干了。
沉默
1997年,王小波生前给朋友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有言:“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无关——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
作者:贾九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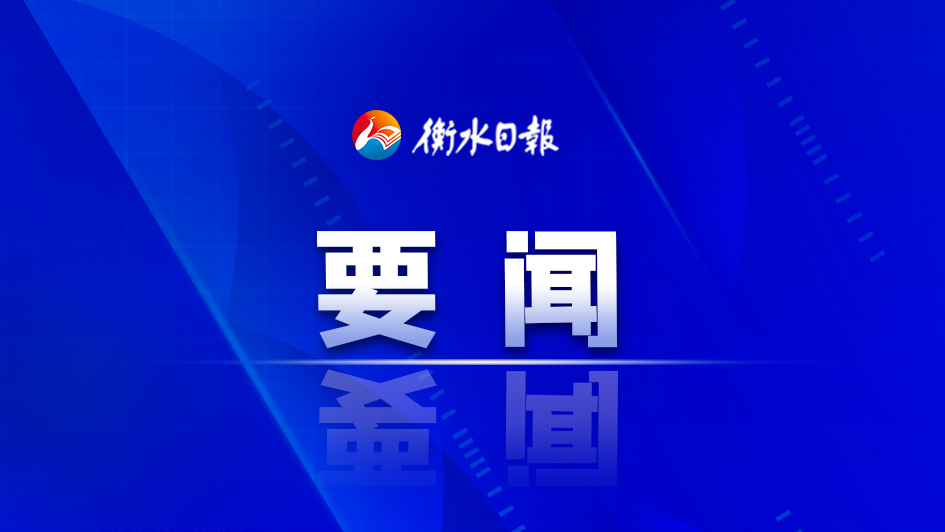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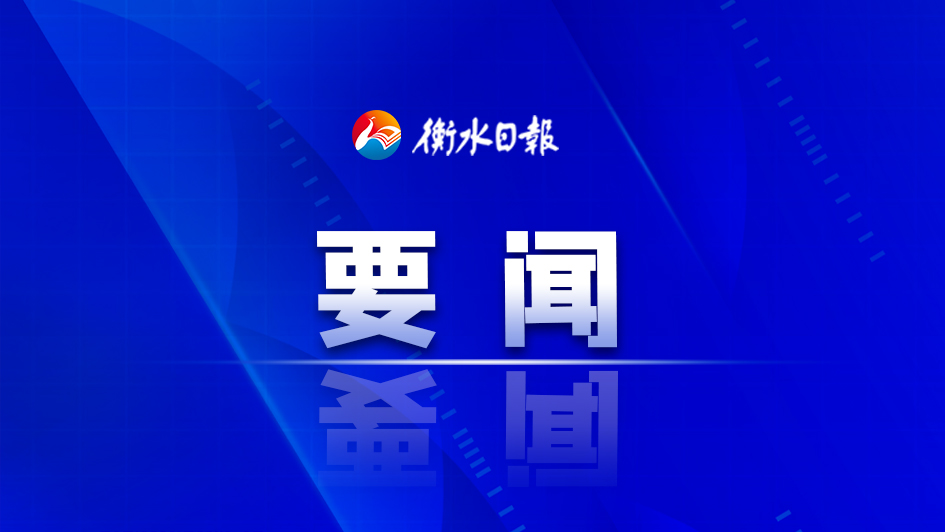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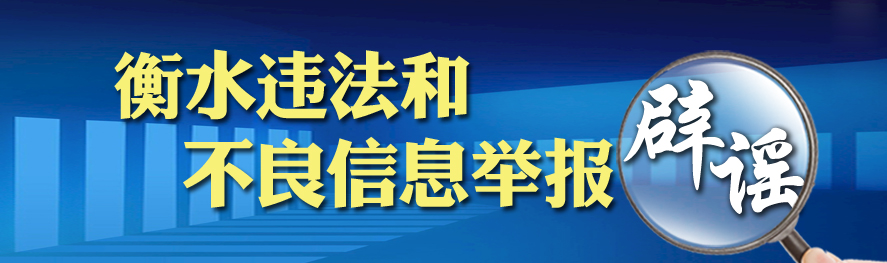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