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平原上的枣强县南吉利村,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有着一幕幕非常值得留恋的场景。
美丽夏日
夏日,村边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塘,特别是在大一些的水塘边,杨树成行,柳树成荫,喜鹊、黄雀、家燕等各种小鸟在树间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中午歇晌的工夫,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里,男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抽烟聊天,妇女则抱着大盆小盆、搓板、衣服开始了她们的“本职工作”。水塘边顿时热闹起来,不时传出阵阵笑声。那些七八岁、十来岁的男孩子,光着身子在水里尽情地玩耍,有的玩潜水,有的耍“狗刨”,有的学踩水,还有的在岸上岸下追打嬉闹,胆子大点的甚至还爬到树上玩起了跳水。这种大的水塘边一般都有供人们生活用的水井,这时人们也悠闲自在地牵着牛、驴、骡马等牲畜,提着水桶来这里饮牲口。酷暑高温,老牛喝下拔凉拔凉的井水,也会愉悦地哞哞哞地叫上几声。整个场景就如一幅美丽生动的图画。
初入学堂
6岁那年,一天,我正和小伙伴宋世坤在街上玩儿,一位大哥哥走过来问我们:“你们上学吗?要是愿意上就去报名。”我认识他,他叫姚西恩,住在我家的东边。我们觉得这事得给家里大人说,不知大人们让不让上。姚西恩大哥哥听后说,那你们就先和大人们去说吧,家里同意了你们就去学校报名。
我回家跟母亲讲明了情况,母亲很高兴,说上学是好事,可以认好多字,学会很多东西,去报名吧。不过,母亲又说,你要说你七岁了,若说是六岁,太小,人家会不要你的,我都一一答应着。不一会儿,世坤找来了,说家里都同意。于是我俩结伴前往学校。跟我们谈话的是一位男老师,后来才知道他是李校长。当问到年龄时,我就按照母亲嘱咐地说是七岁了,谁知,世坤却着急地说,不对,不对,我们俩是同岁的,是六岁。李老师看着我俩认真的样子,微笑着说,不要紧的,六岁、七岁都可以,开学时来上学就行了。
学校的设施很简单,教室里只有破旧的课桌,没有凳子,开学时都要自己带凳子。新生连书本都没有,我清楚地记得语文课本是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用毛笔帮抄写的,当时是抄到第九课。我当时年幼无知,以至于整个一年级、二年级所学的什么,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是谁,都完全不记得了。
砸杆棒儿
农民的劳动观念是从小培养而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从手能提篮,一生的劳作就开始了。三岁就跟着大一点的孩子跑到村外,在大树底下扒开松土,捡拾老鸹虫。老鸹虫个头有小花生豆大,有翅会飞,黑黑的。边扒边找,一个个捡到小瓶里,拿回家去喂鸡。五六岁就要提着小篮,拿把镰刀,去地里给猪砍菜。七八岁就要背起篓筐为大牲畜砍草了。到十来岁就能参与家里、地里的好些事了。这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诠释吧。
冬天,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村边的水塘里结了厚厚的冰,孩子们也不在家呆着,仍继续着自己的劳作。学前学后,女孩子背起篓筐,拿起筢子去拾树叶,男孩子当时很时兴的一项活动就是砸杆棒儿,当柴烧。
一到冬季,小伙伴们就忙开了,积极准备自己的劳动工具——枣木棍,当时的俗名叫友(you)子。枣木棍的长度在60至80厘米,粗细在2至3厘米,直直的,打磨得很光滑,特别是手握的把头部位,手感更好。枣木棍既坚硬,重量也适度,因为是要把枣木棍扔出很高去砸树上干枯的树枝,木棍太轻就没有力量把枯枝砸下来。
那时小伙伴儿们一出去都是三五成群,每人的背筐里都备有三五根这样的枣木棍,一路上连说带笑,连打带闹。到了小树林子,各自仰着头找寻自己的目标——枯树枝。操作时要手握木棍的一头,使劲把木棍投向树上选定的枯枝,把枯枝砸下来。说时容易做时难,就是这点事,既要有力量,又要有准头,还要得要领,没有准头砸不上,没有力量砸不掉,为砸下一根枯枝有时要投好几次。因为是要用木棍往树上投,还经常是枯枝没砸下来,枣木棍却被架在了树上,就只得先用别的木棍砸下架在树上的木棍,还经常为救一根木棍而把自己的几根木棍都架在了树上。这时,小伙伴们就主动过来解救架在树上的那些木棍,不分你我,相互帮忙。
集体劳动开小差儿
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参加支农劳动。一帮孩子,每个人背上被褥,在班主任张炳申老师的带领下,先是来到夏吉利村,后来转到任毛庄村,接着转到张毛庄村劳动。
在张毛庄村,一天晚饭后,我和两个小伙伴儿溜达到村里的代销店,突发奇想,花一块钱买了一瓶果酒喝了一通。喝完酒没回去睡觉,竟回本村各自家去了。在家呆了两天,三个人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一商量,还得赶快回去。第三天中午,我们赶回了张毛庄村,同学们正准备吃午饭。我们提心吊胆,做好了挨批受罚的思想准备,因为张老师是个脾气很大的人。我们主动找到张老师,低声说:“老师,我们回来了。”显然是一副内疚、自责、惭愧的可怜相,然后等着暴风雨的来临。出乎意料的是,暴风雨没有来,张老师只是低沉着脸,闷声闷气地说:“吃饭去吧。”躲过了严厉的处分和惩罚,我们没有侥幸,倒觉得愧疚极了,干起活儿来更卖力了。现在回想起来,张老师的大爱,包含着父爱的刚烈,母爱的温存,于无声处的感化。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想起敬爱的老师和活泼可爱的同学伙伴儿,那些事儿、那些人,仍然回味无穷!
作者:宋振才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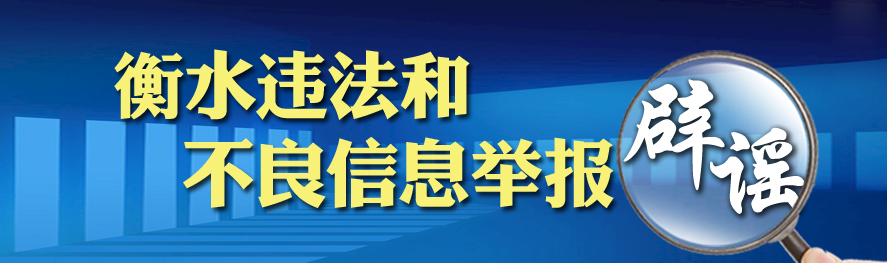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