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有闲,得空和几个儿时的小伙伴聚了聚。在老家那条胡同里,年少的我们如脱缰的野马,经常闹得鸡飞狗跳墙,被左邻右舍大娘大婶找到家里。后来我们懂事了,拿上镰刀背起草筐,走进田间地头以及浓密的青纱帐。我们比赛看谁先砍满一筐青草。青草卖给生产队,可以换取几分钱,用来填补干瘪的生活。
麦收的时候,我们经常跟着生产队的老牛车,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收拾大人们割下的一捆捆麦子。那时麦子是干的,尖尖的麦芒,如同一根根钢针,一不小心就会扎在手上、胳膊上,一阵阵钻心地疼。赶车的老张头手里端着三股叉,把我们用了吃奶的力气也没有扔到车上的麦子捆接住,放到车上,牢牢压住。
老张头五十多岁,圆脸,在常年风吹日晒的岁月里,生成了一张黑红色的脸。这么多年,唯独见了我们这些朝气蓬勃、不知寂寞、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他的脸上才会有笑的模样。太阳很热,就连麦田里的土也是热的,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细嫩的皮肤被麦芒扎得又痛又痒。可我们还是嘻嘻哈哈,你追我赶,看谁干得欢、麦子收拾得干净。
牛车装满了,只有两个人能享受高高坐在牛车上的待遇。坐在上面,整个身子都陷在麦子里,有时只露出头。随着牛车的晃动走出坎坎坷坷的麦田,走上了田间小路,再走上大路。那时的大路没有现在这么宽,也没有现在这么平坦,张老头赶着车,手里扬着鞭子,鞭子只在空中飞舞,说什么也不会落在牛的身上,有时他和我们说着话,可我们坐在高高的麦秸垛上晃动着,看着远方,没有工夫和他说话,无奈他就会放开破锣嗓子唱起来。有时唱小放牛,有时唱宋老三,只要他一唱,我们就会被吸引。就这样,我们随着牛车的晃动来到生产队的场院里。此刻场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麦子,几个上了年岁的老头老太太在紧张地破捆,把一捆捆的麦子均匀地平摊在场院里。有一个老头个子不高,干干瘦瘦的,他是轧场的一把好手。手里一杆长长的红缨鞭时不时扬在空中,两匹生产队的枣红马在长长绳子的牵引下,很听话地围着他转圈,由远到近,由近到远。我们站在场院边上看着,很是羡慕,一个个心里很是痒痒,恨不得跑过去接过他手里的鞭子和缰绳,当一个很出色的场把式。我们为能站在老人身边,双手抓住缰绳让马儿围着自己转圈而自豪。每一次这样的经历,都会让我忘乎所以,足以让我炫耀很久。每次接过缰绳不忘讨好地说:“爷爷,长大我来接你的班。”
“哈哈哈”,每到这时老头就会抚摸着我的头,又拍拍我的肩膀,长长地叹口气。我问:“爷爷你不愿意,不喜欢我?”我觉得很委屈很伤心,一股泪水涌出眼睛,也会撅起小嘴。
“好,好啊!”过了好久,老头才轻声说,“你们是咱村里的接班人,也是国家的接班人,不光是站在这小小的场院里打场、轧场,必须要先好好学习,走上更高更重要的岗位,去建设咱们的国家。”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老头年轻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在部队负伤后,被派到地方武工队担任队长,解放后由于不识字,闹出很多笑话,就自动要求回到村子里,当了一名普通老百姓。这些年从不言说自己的辉煌历史,只是默默无闻地干着农活,成了农村少有的庄稼把式。那时我不懂他说的话,只当他偏心眼,不让我接他的班,我就会扔掉手里的缰绳,跑到场院边生气起来。
“你长大了就会明白。”老人看着我只说这一句话。
打麦场上,麦收时节要紧打、紧收、紧晒,大人们不分昼夜,甚至到家匆匆吃一口干粮,喝一瓢凉水就又赶紧忙活起来。看着大人们整天汗流浃背的样子,我们也渴望自己到场院里干点儿活。有时我们几个孩子喊叫着跑进场院里,不是被厚厚的麦秸滑倒就是被麦粒滑倒,这时大人们就会瞪起眼睛,大声地呵斥我们。其实我们不是捣乱,只是出于好奇,真心实意想帮帮手。大人们不理解,我们也觉得不高兴,长大了才知道在打麦场上干活很苦很累。
去年我们回老家,还特意到生产队打麦场上去看了看,打麦场上长满了浓密的草。此刻小村子里很静,很多年轻力壮的都去城里打工了,街上也很冷清,很少看到孩子们。那些上了年岁的人们,也不再站在墙根,而是骑上三轮车,一天三个来回成了接送孩子们的专职司机。
这么多年了,小村在变,在发展;人们在变,在发展。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从里面走出来的人物、画面、地址和风景,不觉间已经远去,成为了历史。
作者:金秋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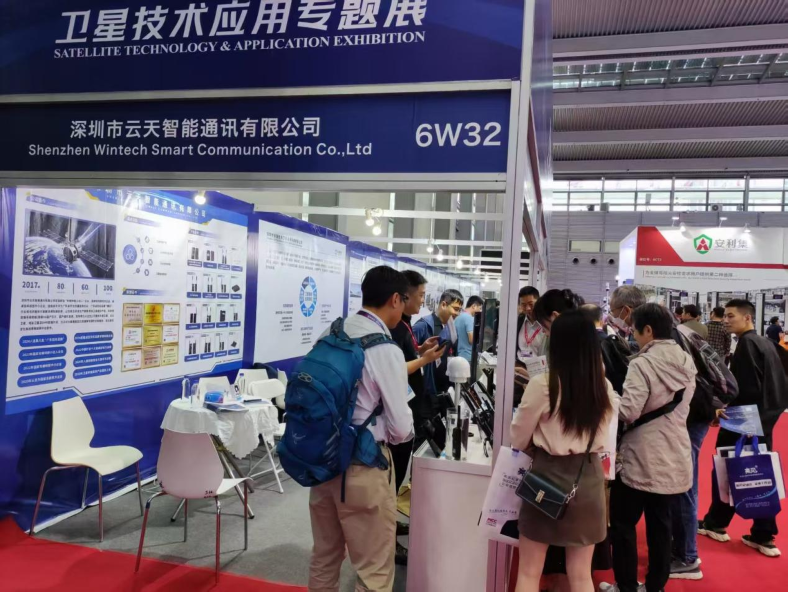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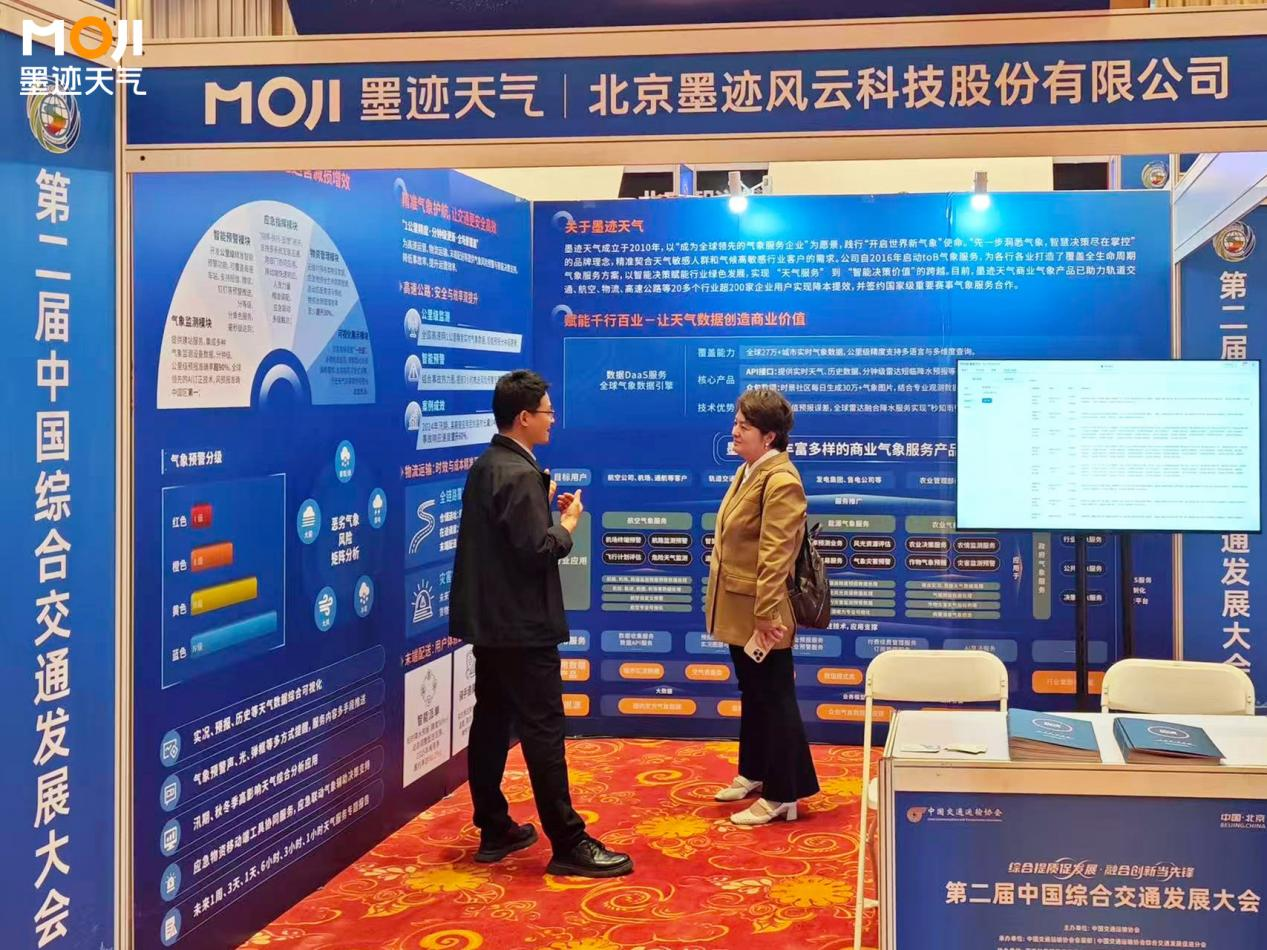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