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日子,在小区散步,一位邻居正用木棍打砸地面上的豆秧子。我问:“自家种的?”他说:“不是,从北沼村的地里拾来的。”他还告诉我,现在收割豆子全是机械化,收得挺干净。他和老伴拾了半天,才拾了这些。我看最多能落四五斤豆粒。看着这些豆粒,想起少年时期和我姨一块去外村拾花生的情景。
我姥姥家在阜城县李高村,我从小在那里长大,也在那里上学。李高村是黑土地,不能种花生。花生对于那时生活在黑土地上的农民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尤其是我们小孩子,更是吃稀罕,拿着当宝贝。逢年过节,家家都买几斤炒熟的花生,预备着招待亲戚朋友。我非常爱吃花生,喜欢那清香可口的味道。离李高村十来里地的漫河一带,就是白沙土地,那里每年都大面积地种植花生。
我十岁那年的秋天,村里好多人去漫河一带人家收完花生的地里拾花生。有一天,姨对我说:“小子,赶明儿你跟我一块儿,咱上漫河拾花生去。”姥姥也在一旁进行“动员”:“跟你姨去,拾多少算多少。”当时,正赶上学校放秋假,小孩子没事干,我很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也不知是几点钟,反正天还漆黑,姨就把我叫醒。我们简单地吃了早饭,带上中午吃的窝窝头。姨扛上一个扒锄子和一条口袋,我拿着一个小镢头和一个小布袋,和村里其他人一块儿,成群结队地向漫河走去。到了人家村的花生地里,天才刚刚发亮。
大家很快找到一块刚收完花生的地,无需人指挥,就排起了长蛇阵,齐头并进地开始刨土拾花生。大人们用扒锄刨,几乎是接二连三地能拣到花生,装进口袋。我也紧忙活,小镢头上下翻飞地刨着,但很少拣到花生。不大一会儿,我就腰酸腿疼,气喘吁吁,只好干一会儿歇一会儿。一个大婶看到后说:“不怕慢,就怕站,孩子,干呀。”我说:“腰疼。”大婶说:“小孩子,没有腰。”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中午,大伙儿就在地里吃点带来的干粮,连口水也没有。
下午五点来钟,大家收工回村。到家一过秤,我姨拾了二十来斤,我那小口袋才刚够五斤。大人们还鼓励我:“行,拾得不少。”
出去十里地,到别的村去拾花生,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其实,拾麦、拾秋,对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是年年都有的事情。秋天拾秋,到地里扒拉着已掰完穗子的玉米秸,只要有玉米粒,大穗小穗都要。去豆子地里捡丟掉的豆棵子,运气好时,可能会遇到豆子炸了捆的,落在地里的一片豆粒子。这时,就把小褂脱下来当包袱,把豆粒收起带回家去。麦季,我们一帮小家伙相伴去拾麦子,凑够一把,就用麦秸捆起来放到筐头里。有时会碰见看青的(生产队指定的看护庄稼的人)叔叔大爷。这时,有一个人一使眼神,大家心领神会,于是异口同声,可着嗓门儿、带着节奏地大喊起来:“拾麦,拾麦,连偷带拽。拾秋拾秋,连偷带丟。”这样做的目的是跟看青的叔叔大爷开玩笑,想让他们听见着急生气。谁知,看青的大人不仅不责怪我们,还笑眯眯得挺高兴,直说:“这帮嘠小子,挺喜人的!”
拾麦、拾秋,我认为是一个好传统。就如我们邻居,进城这么多年了,还保留着农民勤劳、朴实的作风。把地里丟的粮食拾回来,首先是增加了个人的收成,其次是做到了颗粒归仓,再是还锻炼了身体。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去漫河村里拾花生,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作者:费爱民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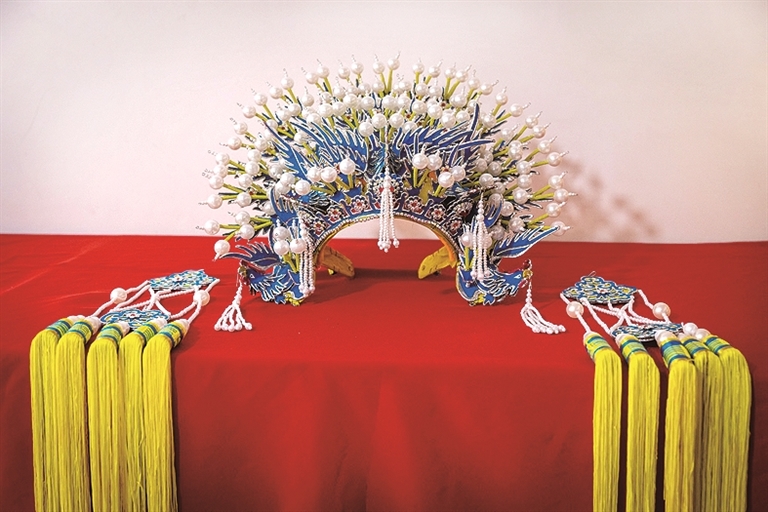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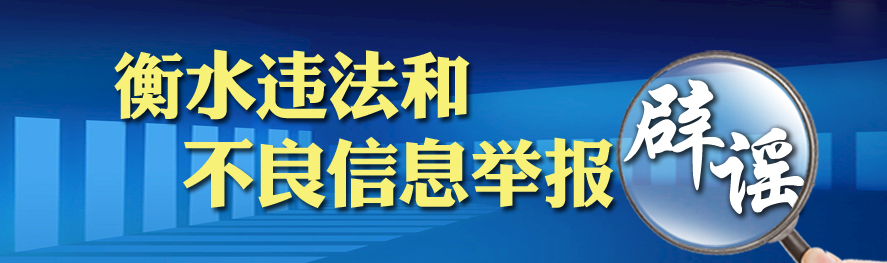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