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孙犁年谱》,发现书中三处写到安平籍作家李大振,尤其是1964年4月的记载非常详细。原文如下:“21日,韩映山、刘怀章来访。谈及:青年作者古怪者多,要注意这个问题。李大振看来挺本分,要注意培养。”
李大振是衡水名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地区文联副主席和《农民文学》副主编。我当时常给该刊投稿,也参加过几次作品研讨会,所以对他有些接触和了解。看到孙犁对他的评价是“挺本分”,倒使我头脑中那些模糊支离的印象清晰起来。
其实,李大振和孙犁这两个名字,我是在1964年一期《河北文学》上同时看到的。那时我正上五年级,语文老师把这期杂志带到课堂,叫我们抄几段描写儿童生活的精彩段落。而这些段落就是摘引自李大振的作品。那期杂志还刊载了孙犁的《业余创作三题》一文(按《年谱》记,此文是孙犁文革前最后一篇文章,同时发于《天津日报》《新港》和《萌芽》)。
少年时期,我对孙犁的理论性文章兴趣不大,但却记住了李大振作品的一些细节和语言。如写一个怯懦女孩,为锻炼自己的胆量,就把本来害怕的毛毛虫放在铅笔盒里,每天故意看几遍,逐步成为勇敢的小姑娘,叫人感到十分新鲜和生动。李大振早年是小学教师,能从亲身经历的生活中构思故事,选择细节,加之语言朴素简练,通俗易懂,自然受到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喜爱。我想,这也是“本分”的一种诠释吧。
李大振的“本分”,似乎体现在他为人处事的各个方面。文革之前,他因创作脱颖而出,被调入河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这是许多基层作者梦寐以求的好事,但他却不太情愿,甚至反复请求回到基层。孙犁对他的这一做法表示了鼓励和支持。“年谱”载:“1981年4月15日,致李大振信。感谢约稿,并建议李下去(从河北人民出版社到衡水地区文联)。工作关系可以保留在出版社。”
李大振回衡水后,协助文联主席李清创办《农民文学》,发展繁荣文学事业,做了很多工作。我就是那时得以与他相识。印象中,他是个处事低调性格内敛的人,每次开会研讨作品,他总是认真倾听别人发言,从不轻易表示意见,更没见他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我的小说虽在《农民文学》发过几篇,但也没听他说过肯定或批评的话。只记得有次参加评稿会,因都要念自己的稿子,当我读完自己的习作后,他仔细听完,未置可否,只是问了一句:“你叫同桂啊?”就没了下文。我曾几次鼓起勇气想说出受他影响而喜欢上文学的经历,但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场合。
李大振虽不张扬,但在衡水文学界的作用举足轻重。饶阳老作家许可常和我说:“《农民文学》的稿子,能过大振这一关就差不多了。”许可和他十分熟稔,并经常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印象中每次总是老许找话题编排他,而他也就笑嘻嘻地听着,并不恼怒,也不急于反击。直到老许说得口干舌燥,他才慢悠悠来上一句:“许——可,谁到你家去,你老婆子也许可吗?”记得许可曾给他起个绰号,总喊他“李大针”。我背地里问老许何意,老许说:“这是我编的歇后语,锄杠把纳鞋底儿——大针。这家伙从省里下来编咱这小刊物,属于大材小用。”
一个作家和编辑,最大的本分就是对作品选材、立意及文字的严格推敲和把关。
1984年,衡水文联和花山出版社联合推出报告文学集《百户农民列传》,曾给饶阳确定四个题目。出书时,其它三个作者的稿子都顺利过关,只有我那篇写养鱼户的《春塘水暖》被退。我拿着删削修改的退稿,找在文化馆工作的许可询问原因。他认真看后说:“大振是本书的责任编辑,这是他的笔迹。既然他改得这样认真,看来原是想用的。之所以退稿,可能是你把阴暗面写得多了一些。”我这篇稿子,开头从养鱼人用柳条抽死吞食鱼苗的水蛇写起,类比致富专业户面临吃拿卡要的压力,如实写了电力税务部门个别人的不正之风。编辑可能考虑这样暴露问题的事例过多,会给传主和作者带来麻烦和纠纷。当时我有些耿耿于怀,不太服气,又据此题材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鲤鱼状》,因水平所限也未发出。后来我反复琢磨此事,逐渐明白了编辑的良苦用心,也理解了他们的严谨和周密。在以后的写作中,我时时提醒自己要认真调查,辩证思考,合理取舍,反复推敲。若如老许所言,此次退稿是经李大振敲定,那我也从这件事学到了他的谨慎和“本分”。
工作敬业,做人实诚,为文朴素,这都是“本分”的题中应有之义。孙犁先生可能也是为此而关注和欣赏李大振的吧。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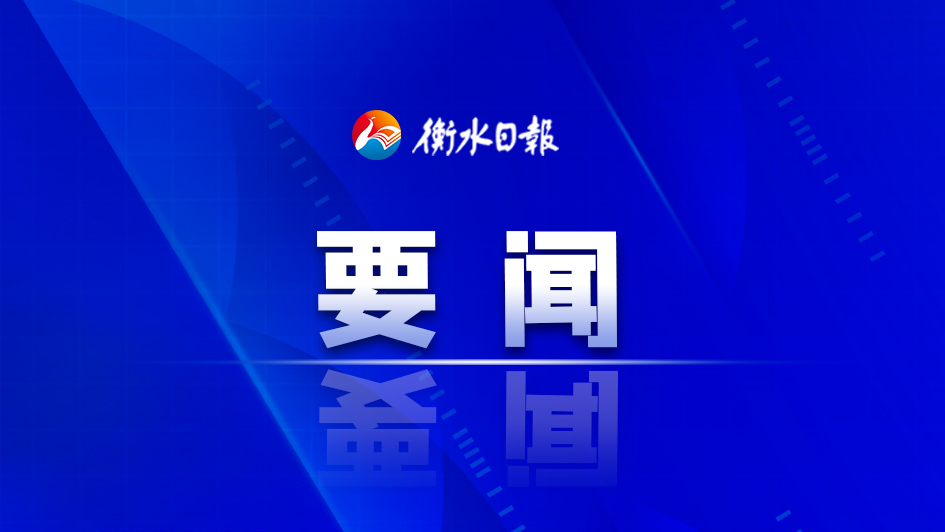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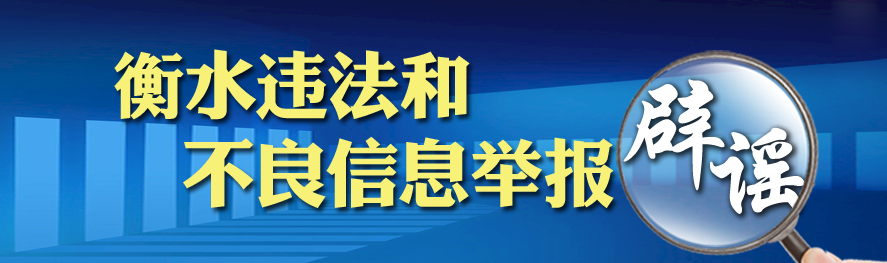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