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娃,个个是掏鸟高手,但也因此担过无数的惊险。
麻雀、蝙蝠把窝做在老旧房的墙洞里;喜鹊、黑老鸹把窝做在树冠上;猫头鹰类则把窝藏在树窟窿里。
小伙伴们上房掏麻雀,不止一次被潜伏在墙洞里偷蛋或偷鸟吃的蛇叼了手。手猛地抽出洞外时,常会带出一条蛇来。但也不必惊慌,我们这方水土产的都是无毒菜蛇。
从树上摔到井里去的,只我一次。当看到窝里的小老鸹时,心头一时激动,便一脚蹬空。那是棵古榆,长得合抱参天,树冠茂盛且龙蟠虬结。怀抱一眼砖井,井口直径约两米。井水幽光闪动,深浅莫测。常年见有青蛙浮卧水面。还幸亏自己从小就敢下河戏水,早早习得了一身好水性。
如今,连农村的孩子都知道,随便捕猎动物是犯罪。过去人没有动物保护意识,只把鸟兽当野物玩耍,只有燕子是个例外。
燕子把窝筑在百姓家,被农家人呼作家燕,甚至比家里供奉的灶王爷还显尊贵,若有谁家的孩子想对家燕图谋不轨,大人任谁看见,都可以捉住就揍。
我和燕子有亲密接触,是在姥姥家开始的。姥姥家有窝燕儿。
比起麻雀那些野货,燕儿真叫漂亮。它体态曼妙,羽衣晶亮,且黑里透着蓝绿。一条半开剪刀似的尾翼,叫人一眼就能把它从云空认出来。
从门上窗棂孔处,大燕儿闪出闪进,跳梭一样灵活。
一口口泥做成的窝,牢牢粘在檩头下的山墙上,形似半个圆球。
一窝待哺雏燕儿,挤成一团在窝里蛰伏着。大燕儿不在屋里时,燕窝里安静得叫人以为是空巢呢。但每当大燕儿衔虫飞进屋时,燕窝里会立刻掀起一阵骚乱。随着一片“啾、啾”的叫声,小燕儿相互推挤着、搅扰着,拼命伸长脖子争食吃。张圆的嘴巴,像初开的黄瓜花一样泛着嫩黄。
当然,对姥姥家那窝燕儿的这番美感,全是出于今天的回忆。自己当年一心想的只是如何用一根竿子把燕窝捅下来,把小燕子弄到手里。
当年虽四岁,尚步履蹒跚,但秉性里专好猎奇弄险,撒野使性,常被姥姥、姥爷视为匪类。
姥姥大概早就在我身上留了一个心眼。当我对燕窝伺机下手时,姥姥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一把夺下我手上的竹竿,折成两截,黑着脸吓唬我,说:“捅燕窝‘发眼’,眼珠子肿成‘猪蛋’大,痛死,还要落成小瞎子。”并举出本村一个大瞎子为证。
姥爷从田里回到家来,受了姥姥几句唠叨,也赤膊来到我眼前,瞪着两个大眼珠问我捅燕窝的事,并故意把两只大手在我面前攥出“咯咯咯”的响声。
我彻底被“镇压”了。那段时间,连小伙伴群里陆陆续续传出的都是被“镇压”的消息,都消停了。从此,再没人敢提捅燕窝耍乐子。
童年真有趣,只是时光太短。像夜空的流星,像雨点打在水面上激起的水泡。
当关童心的门,一旦被人世间的风吹开,那颗童心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片汪洋,那是人生的“海”,是灵魂归处,是有来无回的地方。不管那颗心多么不情愿,也绝难逃脱被那海深掩的结果,而童年的一切记忆,也终究会在这里幻化成一片遥远的云。
十八岁那年,我也被那“风”吹进了那“海”。迈开了进城打工的人生第一步。
姥爷忧心我缺乏独立,手指燕窝,要我向燕子学人生。姥爷说做事要像燕儿一样勤奋,为人要像燕儿一样忠诚。姥爷说只要记住这两点,到哪儿都能吃得开。
燕子的勤奋自是有目共睹,忠诚怎么讲?姥爷说,勤奋本身就是忠诚职守。“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每年到日子燕儿准来。万里关山、人海茫茫,燕儿不寻得旧主人家不入户,无特殊情况,从不易主。这是燕儿通人性,忠诚于情缘。姥爷说他家那窝燕儿就是从老姥爷辈儿传下来的。
几年打拼,几经沉浮,勤奋我是有的,但不敢说有如燕子般的忠诚。打工路上到处充斥着利益计较,而眼见到的多少好情缘,都无耻地出卖给了利益。至亲如父子,至爱如夫妻。脚下的坑太多,总摔倒,遍体鳞伤,傻子也有痛醒的时候。
似乎全世界的人,在今天都在信奉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我也曾拿此真言去忖度姥爷辈们的人鸟情真。
一只燕子一天大概吃掉五百只飞虫,一窝呢?千千万万窝呢?恐怕每天吃掉的虫子要用车皮来装了。过去没有农药,假设没有燕子这类益鸟,庄稼还有收成吗?
今天人类可以用农药来防控庄稼虫害,但从此还有生态链意义上的绿色食品吗?享受大自然的绿色馈赠已经沦为了人类今天的奢望。
燕子无疑是庄稼人的千古功臣,念小学时就学到过燕子、青蛙。但燕子从人类这里也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回报。人鸟共处一室,人类庇护着燕子无忧无虑,才使得燕族兴旺不衰。
这难道还不是蝴蝶和花粉、犀牛和犀牛鸟的生存关系吗?只是姥爷辈们执念太深,时到今日,依然是动不动还要真情泛滥。
还是在县城上班的时候,一天上午回家歇班,阴着天,我骑自行车急急赶出城外。有一段时日不见姥姥、姥爷了,就想先看看他们。但半路就开始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了。土路泥泞,当我扛着自行车,跌跌撞撞地冲进姥姥家时,眼前一幕气得我简直哭笑不得。
一个两根木棍绑成的简易梯子靠在山墙上,姥爷蹬在上面,两手艰难地扯开一块油布,从房顶漏下来的雨水顺着油布直往下淌。油布遮护着檩头下的燕窝,漏水很严重,若没有这块油布的遮护,估计早已覆巢无完卵了。
大燕儿在屋里飞来飞去,十分焦急的样子。姥姥给姥爷扶着梯子,姥爷整个身子都在剧烈地颤抖,带动着梯子吱吱作响。八十多岁的老人怎熬得住这么折腾?随时都有可能摔下来。
情急之下,我不顾尊卑,竟大声呵斥着姥爷赶紧下来,姥爷则急得大声呵斥我赶紧上房堵漏窟窿。姥姥见我俩争执不下,急得大声提醒我:“止不住漏雨你姥爷不会下来。”我便扯起炕上另一块油布,迅速爬上房顶。
我堵完窟窿回屋,把姥爷从梯子上连扶带抱地放在椅子上时,他人瘫作一团。
我气得流着泪,抱怨:“豁着你一条命去换窝鸟值得吗?”姥爷也不作声,却满脸堆积着畅快的神情,好像真是他自己死里逃了生一样。
姥姥、姥爷相继去世,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我也年近古稀。时间流逝了年华,也消磨了锐气。如今,我已从当初的小乡村发展到城市,钱的确也是越挣越多,但来自生活的时时撞击,常使内心感到莫名的疲惫。
一日偷闲,踏秋郊外,一只燕子带着一阵风贴头顶掠过。一丝久违的家乡情愁陡上心头。我想起了家乡,想起了亲人,想起了姥姥家那窝燕儿,还有姥爷为燕窝遮挡漏雨的情形。然而那一刻最为强烈的心念则是:若能躺在二老睡过的老炕上,饱饱睡上一觉该有多好啊。一颗疲惫了的心,也许只有放在情之怀抱里温暖着它,才得已酣然。
回首姥爷辈们,一生虽多劳苦,但因活得简单而一生坦然自得。他们宁愿钱财吃亏,也必争个实诚的名头,到老秉持着“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似乎一生就只为一张脸的情面活着。
仔细想来,人世间的多少温暖和福报,又无不是从这简单中生长出来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大道至简。
相比姥爷辈们,我辈无疑是人生路上的匆匆者。急迫而精致,是数着脚步赶行程的人。未免心累。那一刻我豁然悟到:人,不可以把利益做到精致,不可以把精明活到十分,糊涂一点,或许更能添彩人生。
作者:周会臣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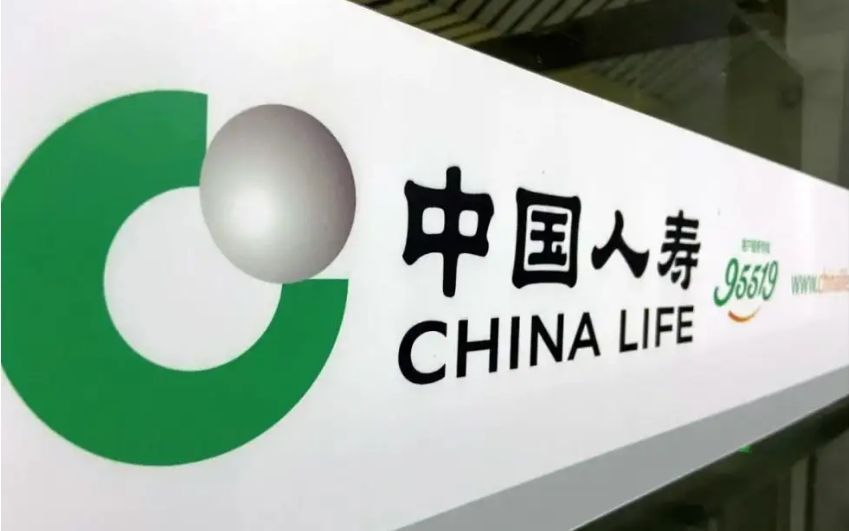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