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淡淡的雾气笼罩在原野上。田喜老汉踏着松软的田埂,查看自家的小麦。
“布谷,布谷”路边枝叶繁茂的槐树上传来清脆的鸟鸣。田喜听到声音,身子哆嗦一下,他下意识里还是把布谷鸟的啼鸣,当做催割的号令。放眼望去,原野的麦子,一片一片,铺成金色的地毯。齐刷刷,鼓溜溜的麦穗,多像白胖婴儿。他揉了揉还有些惺忪的眼睛,搓了搓僵硬的脸颊,咧开干瘪的嘴唇,大吼几声:麦子熟了!苍老而浑厚的声音,震颤着初醒的大地,受惊的麻雀回旋在麦田的上空。
田喜掐了一根麦穗,两只粗糙的大手,旋转着搓弄,吹开麦皮,饱满的麦粒裸露在掌心。他从麦子软硬的程度,确定今天如果太阳足,西南风厉害些,下午就得收割小麦哩!
东边冒出地平线的太阳,酡红的颜色像新嫁娘的脸!
他急匆匆回到家里,像是赶着去汇报重大的新闻。
“大壮妈,快给儿子打电话,说咱家麦子今天就得割。让他赶快想办法!”老汉来不及歇脚,直挺挺地立在老伴眼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
“这么快啊!”老伴从裤兜掏出迷彩色的老人机,拨出号码。
“妈,别着急,我都安排好了,告诉俺爸,在家歇着,该喝茶喝茶,该看戏看戏,今天麦子准能进家!”电话里传来大壮嘹亮的嗓音,似乎他已经看到了麦田的场景,也预料到了父母的焦虑。
“你告诉他,麦熟一晌,虎口夺食!”田喜不放心地嘱咐。
老伴抖了抖前襟的灰尘,瞪了老汉一眼,埋怨道:“大壮啥脾气,你不知道?他说能收,瞎不了。”接着恨恨地说:“还不是你,非得种这一亩八分地的麦子,非得吃新麦现磨的面粉,咱老胳膊老腿费这么大的劲值吗?”
“唉!”田喜老汉委屈地叹息一声,蹲下身子。他何尝不知道大壮的难处!去年,孩子回来过麦一共耽误五天。错过一个大订单,儿媳妇打电话无意间的泄露,却让老两口好一阵儿熬煎。他真的割舍不下对于麦子的渴望,混合太阳滋味、风的味道、泥土腥涩的一捧麦子,让他觉得富足和喜悦。他心里还藏着一幅记忆的图画:平坦宽阔的打麦场上,他挥舞扬锨,不断抛洒出优美的弧线,折射着光芒,金黄的麦子像一场酣畅淋漓的雨,洒落在脚下。也降落在老伴弯腰打扫麦壳的身上。丰收了,金黄的“麦雨”再猛烈些,再持久些。他无数次触碰和打开图画,就像打开他的青春!
中午,阳光火辣辣烘烤大地。西南风汹涌的热浪像火苗伸展的舌头,疯狂舔舐将要收割的麦子。
田喜躺在床上,侧身对老伴嘟囔:“咱年轻的时候,可不敢像这样歇着呢!”
“天不亮,就割麦。早起割麦不扎身子,可是潮,割不快。太阳高了,像下火。麦秆脆,一镰就是一大片。”老伴絮叨。
“你割麦是咱村数一数二的,一晌午也就一亩来地吧!”老伴疼爱地瞅了田喜一眼:“晚上,饭都没力气吃,你在躺椅上就打呼噜。”
田喜哈哈笑着:“再能也比不了机器,我看一两天,村里几百亩麦子就都进家啦!”
太阳敬业地履行职责,将近黄昏,才收敛温度。“今天晚上到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听到天气预报员的提醒,老汉猛地站起来,往外冲去。老伴问:“干啥去?”
“我看看啥时候割咱的麦子!”焦急的语调,使老伴咽下阻拦的话语。
太阳隐没在西边的麦海里,那些熟透的麦穗,弯曲着沉甸甸的脑袋。田喜暗自思忖,要是一场风雨,麦子要遭殃啊!他想到这里,胸口觉得堵塞,鼻根酸涩,眼角涌出泪来。麦子从出苗到现在,哪天自己不来瞧看。它们像是自己的孩子,谁能看着宝贝落难啊!
收割机迈开豪放的步伐,张开巨大的嘴巴,巨兽般吞吐着一块一块的麦子。可是人家是挨着地块操作,这样省时间和费用。虽说机主小五是大壮的发小,自己又怎么张得开嘴巴。一辆辆等待装麦的车辆,都有一家人殷切的等待,自己又怎能不顾乡亲的心情。他拖着灌铅的双腿,缓慢地走。
夜深了,喧嚣的田野停止骚动。那些忙碌穿梭的车辆,也都终止奔波。村庄上空升腾着新麦的清香,田喜老汉吸吮熟悉的味道,心中五味杂陈。
收割机庞大的动静,惊扰老汉的沉思。
“喜叔,开门!把麦子给你倒下!”小五砰砰叩击铁门。
老两口急忙忙地打开大门。“雷沃谷神”雷电似得大眼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怎么回事啊?”
“大壮早就把事交代给我了,我这不,最后割你们的,省的再找拖拉机……”
收割机的仓斗打开,一股急迫的金黄色“麦雨”奔涌而来……
作者:李梦梅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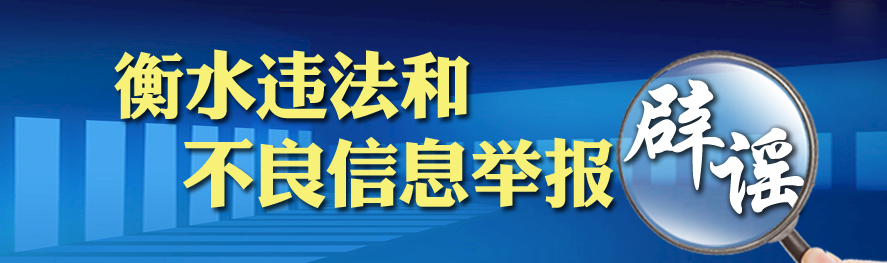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