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州古城墙风光。 王铁良 摄
南门外遗址怀古
1999年,冀州老城南门外
村民挖鱼塘挖出惊天秘密
石器、石凿、石球、石斧、鹿角、红陶杯
沉睡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泥土里
这里,被命名为南门外遗址
石器与石球,通体磨光
虽然原始,简单,拙朴
却是人类进化的标志
冀州史前文明,破土而出
想象着,先民们身着树皮衣
手持石器、石球,捕鱼,狩猎
用奔跑证明丛林里最简单的法则
追逐一头麇鹿
食尽其肉,留下其角
被时光凝固成无言的化石
古朴而苍劲的石凿石斧
平面略呈梯形,横断面为椭圆形
砸向石头,扑扑冒出火星
留下顶部及圆弧刃的残缺
人类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才使得人类脱离了动物群落
那只红陶杯,泥质夹砂
圆唇,敞口,颈部微束,深腹,平底
像个新石器时期的古典美人
多少爱美之人艳羡的目光
被石化成通体的手指压痕
其实,所谓冀州南门外遗址
就在我如今居住的安居小区之下
一把石斧,拍打着史前的波涛
在荆棘乱石中磨砺
劈出九州之首的龙脉经络
冀州古城墙听风
一部《冀州志》
再厚,也厚不过
冀州古城墙上的一块砖
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
再沉,也沉不过
古城墙砖缝里风的一声叹息
站在荒草寂寂的古城墙上
顿感夕阳落幕,林木萧萧
历史的云烟从黄土里奔跑出来
想当年,太守任光打开城门迎纳刘秀
也打开了一个朝代的大门
从此开启“光武中兴”历史新纪元
袁绍坐冀州,风吹旌旗猎猎
千顷洼操练水军,“南向以争天下”
最终击败公孙瓒,跃居中原首强
刺史山涛坚守其节,雅操清明
身在竹林,心和竹子一样清醒
留下竹林寺,常常让冀州人念起
从冀州知州任上走出的李秉衡
受命危难,领四军,痛击八国联军
“固知必不能敌,誓以一死报耳”
清光绪年间,冀州知州吴汝纶
以文化筑城,延续绵长之文脉
吴公渠惠民,千顷洼联通滏阳河
城墙很厚,箭射不穿,刀砍不动
没有软弱的战士
只有软弱的王朝
冀州古城墙,一根历史的骨头
一段永不风化的往事
一条系在历史腰间的腰带
李三娘石磨传奇
来自汉代大山的一块石头
让比石头更坚硬的老石匠
生生劈成了两半
一半是太阳的圆,一半是月亮的圆
天造地设的吻合,同轴,同步
石磨合上,便有五谷杂粮溢出
仙女李三娘谷子一样低着头
双日,于城外海子磨面
单日,为城内百姓送面
她不愿助袁绍兴兵,夺取天下
闻金鸡叫,遂骑神牛腾云驾雾而去
奔向泰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从两汉到隋唐,从宋元到明清
石磨在春夏秋冬中转动
如今,静静躺在博物馆里
地上,大石磨不说话
地下,老石匠沉默
只有李三娘,依然活在冀州人心间
在老盐河,我感受到黄河的脉搏和心跳
河流出发时,就注定不再回头
不管如何改道,也要奔向大海
那奔流不复还的倔强和豪情
足以从天上抵达人间
黄河也曾北流
也曾滋润过枣强、信都、衡水的土地
河水向北冲击,打开河道
七个“开河”老村的遗迹,至今清晰可辨
两岸聚集着朴素的村落
收留下多少艰辛与苦难
有故乡,有炊烟
有高高的芦苇和长长的思念
南宋建炎元年,北流黄河终断
改南流,转东流,入黄海
黄河水不再恩泽衡水
渐渐,河底积聚起厚厚的盐碱
幸好,这里没有被漳河或者
其他河流侵占和冲刷
从此,黄河故道变身老盐河
一群将黄土穿成衣服的人“淋小盐”
传说中那十八只木船上的盐
都融化在这条大渠里
“南田”“北田”“王家口”“李家口”
这些浸透盐味的村名依然新鲜
老盐河,历史遗留在衡水的一段记忆
有着黄河的脉搏和心跳
原来,我们也在母亲河的怀抱里啊
曾经那么近,又那么远
吴公渠,一个教育家的治水往事
上古,大禹治水自冀州开始
晚清,吴汝纶也在冀州治水
是上天的约定,还是历史的契合
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礼赞
你引千顷洼之水,入滏阳河
浩浩荡荡,自南而北,带我们飞
把一个教育家的血脉融化进去
弹奏出亘古未闻的和谐乐章
飘扬的名字,流动的曲线
沿着青筋暴凸的手臂蜿蜒而行
龙行大地,一路洒下福祉
千亩斥卤之地,变为膏腴良田
今天,我在吴公渠上怀念吴公
感叹人与水的生动切磋,相互给予
吴公闸如一位老者端坐在入口处
看千顷之水,怎样涌入河的臂弯
人说“奇迹无法复制”
我虽不肯相信,却也信心满满
当年吴公的子民,在与大自然对决、博弈之后
又回到对大自然的感恩和敬畏
夕阳用一双筷子夹住吴公渠
却舍不得一口吞下这斑斓的美
两岸的翠绿红紫,随流水一路奔突
一群野鸭在开阔处,叫得天高水远
吴公渠,一枚流水收藏的书签
铭记着一个教育家的治水往事
脉管中的血液依旧喧响
在岁月的长河里,波光潋滟
作者:杨万宁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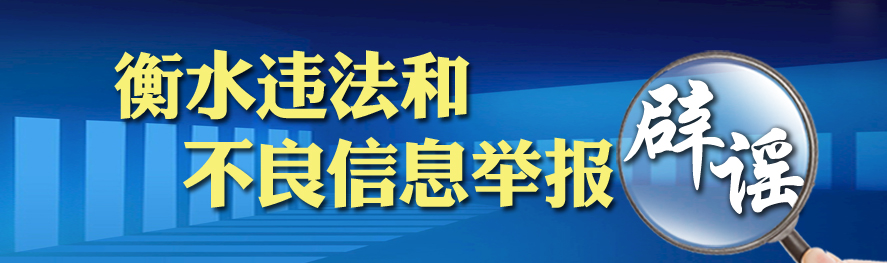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