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聚一散,一顿饭之间,几乎概括了人生百态:校园中的四年时光,宿舍中的朝夕相伴,不知结下了多少的恩怨情仇,终于都要在一顿饭里划上句号。以“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的互相戏谑开场,到酒酣耳热时为高潮。最后,血管里奔腾的乙醇,终于冲破了泪腺的最后一道防线,洗去了脸上的强颜欢笑,离愁别绪从脸上所有能流出液体的孔洞喷涌而出,在这个湿热的盛夏夜晚,最后一次借着紧紧的拥抱,把温热的眼泪和鼻涕互相抹在彼此的身上。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毕业聚餐也好,散伙饭也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高考更像是一场成年仪式,尽管它当然不像高考那样充满了拼搏和紧张的气氛,但相比高考是向中学时代的告别,大学的毕业聚餐,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学生时代的终结。

《一起同过窗》第一季(2016)剧照。
无论是否愿意,这一顿饭后,校园生活就成了永远的过去,再没有人替你点名签到,再没有人叫一声“爸爸”就能给你从食堂带回一份热腾腾的饭菜,甚至你想通宵手游都不能现场抓来几个舍友一直嗨到天亮。
尽管这顿饭后仍然会有无数场聚餐,但以毕业聚餐为分界线,过去的那种专属学生时代的感觉,却永远地不复存在了。那种感觉就像是端起酒杯时一张张嬉笑怒骂的、鲜活的脸,在放下筷子后,突然戴上了冰冷空洞的假面具——毕业聚餐也是与过去真我的一场告别仪式,是踏入成年人所谓世故、成熟的社会前最后一次真情的放纵:“什么也别说了,这四年,都在这顿饭里。”
(关注书评君的朋友们应该记得,在这个毕业季,我们前不久发了一篇《校园罗曼蒂克崩坏史》,这是我们的记者李夏恩写的大学校园爱情故事。在两年前,他还写过开学见舍友的文章《“我是天津人。” “那你会说相声吗?” 》。这两篇文章都基于他十多年前上大学的经历和见闻,在文章发出后,我们收到不少朋友留言催后续。现在,后续终于来啦!)
01
今天的欢聚,明天的散伙
“大学四年,我们一块儿吃过197顿饭,一起醉过161次,在这儿,我真醉137次,装醉24次,吐到寝室97次。二哥,你帮我收拾过63次;航哥,你帮我收拾过24次;飞哥,你一次也没有帮我收拾过,因为你总是第一个吐到寝室的。”
2014年,6月,毕业季。一部名为《寝室》的微电影在网络平台上登陆。平心而论,它的表现手法太艺术,光影明暗的精心布置,将乱糟糟的男生寝室硬是变成了一幅活动的伦勃朗油画。这也让大学毕业这个大众话题成了一件看似精巧而小众的艺术品。在专业发布微电影新作的网络平台“新片场”上,这部微电影的播放量是13.2万,但却收获了1900条点赞和2122个收藏,差不多每70个看过的观众就有一个点赞,至少有三个翻拍的版本。
令人着迷的是这部电影设计的剧情,诡异、阴暗和凄凉似乎都不足以形容,因此一位转发的观众将它归入了“悬疑”之列。这是一场寝室里四个兄弟航哥、二哥、飞哥和六子的毕业聚餐,在没有空调的宿舍里,火锅沸腾,杯盏交错,热气和酒劲熏得每个人脸上通红,不胜酒力的六子横在地上,而二哥和飞哥却在酒精的怂恿下撕下了平日里嬉笑的面具,从学生会,到保研,再到找工作,平日里的冲突在聚餐上集中爆发了出来。二哥敲碎酒瓶把飞哥抵在桌子上,厉声痛骂他平日里让人看不过的种种嚣张做派。
二哥也吐露了他的内心:“我们从这扇门一出去,就都离散了。咱们都得变得社会,变得圆滑,变成自己曾经最瞧不起的那种人。也不是自己有意要疏远谁,但是看着自己曾经熟悉的兄弟,现在和别人说着一些自己听不懂的话,做着一些自己看不懂的事儿。没有了共同利益,也就没有联系了。说断就断了。”
二哥的倾诉,说出众多毕业生聚餐时的心声,所谓的聚餐,就是散伙,吃完这顿饭后,四年交汇在一起的情谊因缘就被一刀剪断,每个人都要踏上自己不同的道路。如果说校园是滋长和培育梦想的地方,那么社会就是一把镰刀,像刈除杂草一样将昔日狂放不羁的梦想一一斩断,只留下适合社会这片土壤生长的部分:不再有烂漫却无用的野花,只有整齐划一、可供一茬茬收割的庄稼。这是毕业让人恐惧之处,但也是毕业让人憧憬之处:梦想也有可能本身就是庄稼,未来会结出怎样的果实无人知晓。
失望在于无力改变,希望则在于事在人为。这种复杂的情感,就融汇于一顿饭中。毕业聚餐之所以少不了喝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不希望自己太过清醒地面对这个太过现实的社会,不妨用醉意当成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过渡。《寝室》的导演程浩,显然深得个中三昧。这位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在一次采访中坦承,《寝室》的最初构思就来自于大三聚餐时的一次醉酒。这让他在醉意营造的幻梦中灵光乍现,既然自己骂了这么多年电影,是不是应该自己拍一部?校园时代的单纯与梦想,社会的圆滑与世故,两者之间如何才能调和在一起,真的需要一顿聚餐。
毕业聚餐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此。而这也是人类之所以聚餐的意义之一。就像钱锺书论吃饭的妙语:“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摩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聚餐让不同的人置于一桌,在同一个盘子里夹菜,在吃饭这一刻,不同可以转化为相同。只要一句“吃吃吃”,就能消弭许多矛盾。大家同吃一桌菜,在初民时代,就是一种集体认同的标志。16世纪的历史学家卡萨斯探访拉美的一处原始部落时,发现融入当地部落的最好方式,就是跟他们一起吃饭:“他吃我们的食物,他就是自己人。”
而在历史悠久的中国,这种化不同为大同的热烈而亲密的聚餐,被语言学家王力戏谑地称为“津液交流”:
“中国有一件事最足以表示合作精神,就是吃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讲究同时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节奏来。中国人之所以和气一团,也许是津液交流的关系。”
当然,从卫生学的角度,津液交流的聚餐问题巨大,远不如分餐更加符合卫生之道。在分餐制甚嚣尘上的时代,反对聚餐的一个最常举的例子,就是“半碗酱油”的都市传说:一个吝啬之家(奇怪的是这个家庭经常安排在山西或是上海),吃饭时只用半碗酱油当配菜。用筷子头蘸一下儿酱油,在嘴里吮吸吮吸滋味,就一口白饭。就这样吃了一年,最后半碗酱油竟然成了一碗。纵然这个例子令人肠胃反向运动,但聚餐对中国人来说,就像爱情的接吻一样必不可少。津液的交换虽然在杯盘之间热闹进行,但还有什么比吃进对方身体分泌的一部分更能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无间呢?尽管《寝室》的导演程浩很可能并未读过王力“津液交流”的高论,但他在电影中毕业聚餐,选择大家一起吃火锅,真可以说是向这一伟大的聚餐传统致敬。火锅涮菜,筷子从锅中夹起,放进口中,又放回锅里,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热情似火的津液交换的聚餐仪式了。
更何况,这毕竟是校园生活的最后一顿饭,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与自己亲爱的兄弟进行如此深度不分你我的津液交流。四年来的所有情感,都只能在这一顿毕业聚餐中寻找发泄的机会。今天的欢聚,明天的散伙。时间必须要前进,无论前途究竟是什么,无论情谊是何等的令人不舍,但毕业后的明天,终会到来。除非像《寝室》电影里那样,强行将时间定格在毕业聚餐的那一刻。电影的结局既令人心悸,也令人叹惋。二哥向飞哥倾诉衷肠之后,举杯相碰。这本来会是个略带感伤的结局,但就在下一幕,两个人突然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六子却从地上爬起来,对着死去的二哥、飞哥,还有躺在床上,身体早已冰冷的老大航哥,流泪数着过去四年里,大家一块儿吃过的197顿饭,一起醉过的161次。校园的生活太值得眷恋,寝室的兄弟也太值得相守,所以他杀了他们,也给自己斟上了一杯毒酒:“我们再一起走一个。”
拒绝明天的选择,注定只能是个悲剧。因为毕业并不仅仅是与过去告别,也是为了向明天招手。无论明天是眼泪,还是欢笑,这顿聚餐,都算是一场毕业后无数聚餐的预演。
02
“最后一次”的放纵
程浩的《寝室》令观众出乎意料的结局,为他赢得了半夏国际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的提名,也让这位年轻的毕业生走出校园,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但这部电影的翻拍之作却没有那么幸运。其中一个翻拍团队甚至险些遭到学校的处分。影片挽歌一般的结局是部分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毕业聚餐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有其原罪。大学期间的最后一顿聚餐,万一行差踏错,纵使不会出现影片结局那样令人心悸的悲剧,也足够让即将跨出校门的毕业生和即将卸掉对他们监护责任的学校头疼不已。
“有人趁着酒兴朝地上摔瓶子,另一个系的一个同学出来制止,为此引起两个系、一百多学生打群架。霎时,瓶子、盘子满天飞。”
1988年7月这场发生在北京某所重点大学毕业聚餐上的闹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最终的处理结果,“十几名主要肇事者分别受到党纪、团纪、学纪处分,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这个案例被写在一本1988年出版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作为书中“毕业前夕须防放纵”的重点揭批案例。尽管毕业这顿聚餐,于情于理,都必不可少。然而,令人匪夷所思,却又看似同样合情合理的是,尽管毕业聚餐对双脚踏在校园和社会两端的毕业生来说,意义匪浅,但在那些步入社会多年的人眼中,毕业聚餐又是毕业季最容易遭到指责的对象。每一声批评听起来都振振有词。最常受到抨击的,就是所谓的“过度放纵”:毕业季是情绪的放大镜,过去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长年隐忍,很可能会趁着即将“各奔他方”而不再顾忌,以致一点小事也能引起轩然大波,而毕业聚餐上必不可少的饮酒,更会推波助澜,使人丧失理智,放纵情绪,酿成悲剧。
当然,毕业聚餐的放纵不仅表现在饮酒上,还包括所费不赀的聚餐费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本发放给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中,就对“毕业聚餐的高价化”大加批判,“校园餐馆客满,邻近的饭店也生意火爆,几个人小聚就得上百元,如果稍微像样点,就要几百元”,这些餐馆甚至还采取各种招揽手段纵容毕业生的高消费,“据调查,校园餐馆一般到午夜12点才关门谢客,一些餐馆为了招揽顾客,还告示:凡毕业生一律八折优惠。”这本指导手册更指控了三项罪状“加重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扰乱正常的校园秩序”“助长学生的拜金主义思想”。
2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物价的飙升,毕业聚餐的消费也水涨船高。在2018年《记者观察》刊发的一篇报道,直接用《毕业季变“烧钱季”》作为标题。记者访问的一名山西大学毕业生自称“5月份我聚餐差不多花了2000元,6月份估计还会更多。”另一名太原师范学院毕业生,“已经在毕业季花费了3000元左右”。根据记者估算,“班级大聚餐、学弟学妹道别、社团聚餐、好朋友小范围聚餐,虽然每次聚餐都是大家一起出钱,花费也不过百元,但是整个毕业季在聚餐、请客上的花费加起来也要1000元到2000元”。这已经是20年前的10倍。报道将这种烧钱式的毕业聚餐高消费,归结于“社会奢华风气延伸至象牙塔的一种表现”。
从过度放纵,到拜金主义,再到如今时髦的消费主义,毕业聚餐可谓“罪孽深重”,因此,有些学校会针对学生聚餐特意制定规章制度,严格管控,也就顺理成章。其中,曾经一度成为热议焦点的,莫过于武汉科技大学在2013年出台的《学生聚餐管理规定》。根据规定,学生聚餐必须提前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填写《聚餐审批表》获得批准后方可聚餐,未经批准的私自聚餐者将遭到处分。白酒被完全禁止,饮用啤酒饮料也必须适度。而毕业聚餐时,“辅导员或班主任必须全程在场”。整篇规定读下来,不得不让人怀疑规定的制定者是不是一位资深中国法律史或是秦汉史学者,不然绝对想不出这种把两千年前专制时代汉代律法中“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的禁令,搬到了21世纪的现代文明社会。
尽管《武汉科技大学报》自豪地宣称规定出台后,“在网上广受关注,深受好评”,但想象一下毕业聚餐时,班主任和辅导员全程在场,像监视器一样紧盯着你手中酒杯的那种莫可名状的气氛,就足以让人脸上黑线齐出,提前戴上了一本正经的尴尬面具。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2016)剧照,图为毕业聚餐场景。
不可否认,这一规定或许会受到那些不喜欢聚餐、不喜欢闹酒,爱独处胜过喧哗热闹的学生的支持,但如果年轻的心灵只被允许保持理性和冷静,却禁止狂放和不羁,那么年轻究竟又有何意义呢?打破牢笼,越过藩篱,去寻求更广大的空间,青春的意义,正在于它本应有旺盛的时间和精力去探寻和创造可能,狂放和不羁在很多时候不仅是应当的,也是必要的。当然,前提是不要越过社会和人伦的底线。聚餐中的嬉闹、欢笑,甚至偶尔的喝醉,以及醉酒醒来后的头疼,未来都会成为青春时代珍贵的记忆。
与之相比,成人世界要求的更多是秩序与规则,是安守这些规则和秩序划定的界限,是随时随地提醒自己不要逾越界限,尽管那有可能会发现新的天地,但也更可能是你无法承担的巨大代价——一个秩序化的社会里,对人的要求是安分守己,而不是尝试冒险,不然,他就会被大多数遵守秩序的人视为异类,遭到排斥。而学生时代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但他们拥有犯错资本的同时,也具备了尝试的勇气。刚刚毕业、不谙社会的学生,带着这股勇于尝试的进取心,扎入其中,很可能会处处碰壁,最终捂着脑袋学会遵守规则和秩序。
但此时,他所遵守的规则,已不再是进入社会时的规则——不断地尝试和冲撞,会扩大,甚至突破社会规则和秩序的外延,让社会发生变化。而这正是社会进步的方式。如果从一开始,学生就学会了在牢笼中安守分际,那么这些带着牢笼进入社会的毕业新人,只会是重复那些将规则秩序加在他们头上的前辈的足迹,亦步亦趋。一切都不会有改变。
毕业聚餐,很可能是进入这个充满规则秩序的社会前,最后一次狂放不羁的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放纵自己内心的机会。就像出征前的将领“醉里挑灯看剑”,在大学四年里被反复磨砺、锻造,即将出鞘的宝剑,在带着天真,甚至有些鲁莽地刺向社会壁垒之前,或许也应该抽出来,在毕业聚餐的微醺中,透过反光,照见那个仍然未失梦想的自己。谁又愿意在拔剑顾影自照的纵乐得意之时,发现旁边站着自己的老师呢?
03
餐桌上的紧张与尴尬
毕业聚餐时最不自在的行为,就是与学校领导和老师同坐一桌。这绝对是一场对意志力的考验。你要提前扮演社会角色,而且是社会等级最底端的那个角色,你要准备敬酒,还要准备合适的敬酒词,你不能在领导或老师夹菜之前伸出筷子,哪怕你早已饥肠辘辘,也只能戴着假笑的面具,等待正在和身边谈笑风生的校领导和老师动筷才能开动。这样一顿饭所消耗的能量和死伤的脑细胞,绝对不是餐桌上那几筷子礼节性的菜肴能补上的。于是,你只能出门找个小饭馆再找补一顿。
毕业聚餐时和老师同桌令人尴尬,但如果桌上全是老师只有你一个学生,那么可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区区笔者,在研究生毕业时,就是这场聚餐灾难的亲历者之一。当年惨痛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答辩结束,我的导师执意要我请一次客,对答辩委员会的三位老师表示感谢。尽管我只是一个穷学生党,尽管我的导师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老板”,尽管我深知他非常喜欢吃饭时组织繁琐的敬酒仪式还喜欢即席拍照。但我仍然天真地相信他应该不会为难我一个穷学生。而且加上他也只有四位老师,按照当年的消费标准,四百元应该到顶了吧?
于是,那天下午,我坐上了导师的车,我看着车辆开过一家又一家饭馆,每经过一家看起来高端大气的饭店,我都会使劲咽一口唾沫。出乎我意料的是,车子竟然开出市区,开到了郊外一家农家乐餐馆。
我只看了一眼竹木建造的精巧的亭台楼阁,便知道我这个月的生活费都要搭在里面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令我瞠目结舌:我的导师居然还叫来了一位在另一个学院里做行政工作的师姐。而他请来的另外三位老师,也没有孤身前来,而是拖家带口,最夸张的一位竟然除了带自己老婆和孩子之外,还叫了一名自己的学生跟着一起吃喝。
我一边看着导师拿着菜单跟人谈笑风生,一边在心里计算自己这个月还能剩下几个钱吃饭。我应该感谢我的导师自己带了酒。菜过三巡,酒过五轮,我在旁边胁肩谄笑,冷眼看着他们大嚼特嚼我的生活费和辛辛苦苦挣来的打工钱。吃到中间,这群人竟然又叫着想喝鱼汤,吩咐我去选鱼。我来到后厨,问厨师哪种鱼最便宜。他想了想说:“老鼠鱼。”我咬着牙点点头:“好,老鼠鱼好,就它了。”
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和这位导师联系过。我的一位同门跟我聊天时,说:“老板跟我抱怨你,说你逢年过节连个电话都不打,太不懂规矩。”——“我给他打电话?难道我还要问了他的地址千里迢迢给他寄咸带鱼吗?”
当然,我的遭遇毕竟只是个例。并非每个老师都像我的这位导师一样,如此精通“社会规则”。我的大学老师,与他完全不同。那是我另一段铭感在心的聚餐记忆。老师骑着一辆摇摇晃晃的破自行车在前面,我们几个同学骑着同样的破车跟在他左右,一路谈笑。最后,来到一家小面馆前。我们坐下,老师掏钱一人叫了一碗面条,又叫了汽水、拍黄瓜和牛肉。没有啤酒,只有无拘无束吃得大汗淋漓。之后,我们来到旧书市场,跟着老师一人淘了几本旧书:
“考研也好,工作也罢,希望你们还能喜欢看书。遇到难事,不嫌我唠叨,就给我打个电话。”
我们毕业,我们各奔东西,我们各自踏上自己的前途,我们在校园并肩而行,命运的线在四年中交缠在一起。一切的一切,犹如电影一般,我们既在各自的电影中扮演主角,也在对方的电影中扮演主要配角。这顿饭后,我们又要各奔东西。聚餐也好,散伙饭也罢,我们已经成为了彼此的一部分,毕业后的未知之旅,我们并非孤身一人。
我们永远是我们。
编辑:李耀荣
来源:新京报客户端原标题:“毕业聚餐”的情绪崩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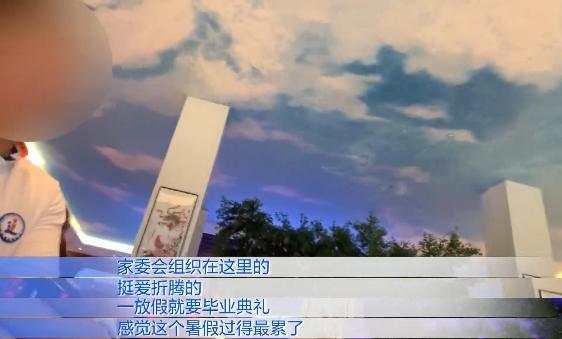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