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徐俊岭是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1945年参加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武强、献县、深县、安平县委工作,一辈子信仰坚定、忠诚于党,对工作兢兢业业、清正廉洁,为人宽厚善良、忠孝感恩、重情重义,是我们子女后辈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每逢清明倍思亲。转眼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我对父亲的思念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相反,伴随着对人生更深的感悟,我对父亲的思念越发深重。
父亲信仰坚定,先国后家,一生忠诚党的伟大事业。父亲参加工作时正值战争的年代。1947年,我祖父去世,父亲正跟随组织在外地工作,祖母让我三舅爷去找他,结果寻了3个多月,找遍了献县、河间、任丘、沧县等多个地方,走了上千里路,也没有找到我父亲和他的队伍。直到半年后,他请假回家,才知道我祖父去世的消息。等我父亲处理完家里的事,再找队伍时,队伍又临时转移了,父亲无奈回家,当起了村里的会计和民校教员,继续为党奉献。1961年,原深县一分为二,分为深县和安平县,县委书记王瑞璞非常器重我父亲的坚定信仰和能力、才华,四次变换工作都带着他,这次又一起从深县到安平工作。
1966年腊月,我祖母病重,怕见不到我父亲最后一面,就给他拍了加急电报,说“母故,速归”。父亲本来就由于没能给我祖父送终而心有遗憾,在得知我祖母的“死讯”后悲痛万分。从公路下车几百米就是我们村,父亲还没进村就大哭,村口的乡亲告诉他,先别哭,你娘还没死呢。父亲赶紧跑回家,此时,我祖母的瞳孔都已经开始扩散。正当我父亲准备尽最后孝道的时候,第二天,安平县委的电报却突然到了,上面写着“情况有变,速归。”此时,一个艰难的抉择摆在我父亲面前,如果回安平,就不能给母亲尽孝送终,但如果不走,关键时候没有回到工作岗位,就辜负党的培养!父亲拿着电报,一边思考,一边大口抽着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母子连心的祖母感受到了父亲的焦虑,颤抖着双唇,把他叫到床前,用微弱的声音在我父亲耳边叮嘱道:“岭子,你是公家的人,上级让你回去,肯定是有大事。你放心,家里还有魏年(我的母亲)和你弟弟,你回去上班吧!”“忠孝不能两全”的话虽然说起来容易,但那割舍不断的亲情放在自己身上,还是让父亲心里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祖母开明大义的话稳定了父亲的心绪,他又在自己母亲身边陪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郑重地给我祖母磕了头,就眼里噙着泪水回安平去了。就在父亲走后第二天,祖母与世长辞了。家里派我两个堂叔去安平通知我父亲,谁知道,他们骑自行车赶到安平时,正看到我父亲被戴着高帽子在汽车上游街批斗呢,见此状,吓得他们调头就回来了。直到半年后,父亲才脱身回家,直接到我祖母坟上恸哭。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错过了为父母尽孝送终,成为了父亲一生的遗憾,但也充分体现了父亲坚守信仰,先国后家的高尚情怀。
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逊、诚实、有才,留给与之相处同行极深印象。父亲有两样“绝活”,一是同志们公认的“笔杆子”,二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出自他手的材料朴实无华、缜密规范、语言流畅、字迹隽秀、结构严谨,深得领导赏识。60年代初,他在安平县工作,县城还没有电灯,晚上写材料都是点烧煤油的泡子灯。后来条件稍有改善,由县面粉厂带一台小发电机,前半夜有了电灯照明,后半夜停电后,他的屋里还经常亮着油灯。他有抽烟的嗜好,特别是写材料几乎一支接一支。常常是写着写着没词了,点上一支烟,深吸几口词来了,把烟往桌上一捻继续写,第二天清晨桌子上便留下一大堆半截烟头。安平的一些重大报告、重要讲话,许多典型材料都出自他之手。许多同事回忆起他趴在办公桌上点着油灯写材料的形象,都印象深刻。据他当时的同事崔根乱(曾任武强县委书记、衡水市政协副主席)回忆:1971年下乡,发现当时在全县很有名气的一个生产大队存有不少问题,想向县委反映一下,以期引起领导的关注,于是向县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为了充分说明自己的观点,便列举了该大队存在的问题。为稳妥起见,先让徐看了一下,徐看后在报告开头加了一段话:“该大队无论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还是农业学大寨、生产建设等,都是不断发展的、前进的,这是必须肯定的,”并对崔说:“写材料不仅是文字上的功夫,还得懂得辩证法,不要有片面性”。时过三十年,经他修改的这个草稿仍然保留。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称他为“老徐”,也兼有兄长、师长双重涵义。
父亲在工作上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时时处处防微杜渐。在父亲所接触的人中,无一说他搞不正之风,而说他敢于抵制歪风邪气的大有人在,有人甚至称他“倔老徐”。1972年后,父亲在安平担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劳动人事工业、交通等许多重要部门,手中有一定的权力,但他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1977年,组织上给干部家属办理农转非,在那个年代,农转非就意味着吃上了商品粮,孩子长大后给安排工作,一辈子有“铁饭碗”。按照政策,全家只有母亲和弟弟符合条件,他一心为公、坚持原则,始终没有利用手中的特权对我和三个姐姐进行照顾。父亲当时有一件最心爱的“宝物”,那就是他下乡用的一辆日本自行车,曾为他下乡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每天都擦得锃亮,可见其心爱程度。由于我和弟弟上学,母亲没有工作,我们一大家子的生活全靠父亲每月80多块钱的工资支撑,生活十分艰难,只要他张张口,就不愁吃穿,但他坚决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硬是像割身上肉一样心疼地把自行车卖了,来解决家庭的生活费用。
父亲对生活感恩,对父母孝敬,对子女严格教育,为后代传承好家风。我祖母有兄妹6人,因为我祖父去世早,父亲又常年在外工作,家里的生活得到了舅爷们的很大帮助和关照,父亲和二叔都深怀感恩之心。每次他从安平回家,都精心准备,带上一些好吃的和零花钱,骑自行车先到到深县溪村看我姨奶奶,再到武强潭封庄去看我舅爷,直到天黑才能赶到家。这条路就成为了父亲和二叔的“感恩线”,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他一走就是十几年,直到老人们离世。在父亲眼里,孝道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责任。他每次进家一定先到自己母亲那里报到,并且尽量多的抽时间陪她,经常拉家常到很晚,甚至是在我祖母几次催促下才回屋睡觉。父亲和我二叔的感情也特别亲,二叔要有什么困难,父亲都千方百计地去解决。我姐弟5人,二叔家有6个孩子,我们十一个姐弟也团结和睦、不分彼此,父亲真心爱护、关爱整个大家庭,尤其是在那个特殊困难的五、六十年代,挣的工资也大部分补贴了整个大家。在对待后辈子女教育方面,父亲又严格要求,将感恩、孝道、忠诚、善良的家风一脉相传,为我们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当年,我大姐和堂姐一同在石家庄戏校学习,父亲出差到石家庄,抽空去看她们,给她们一样多的零花钱,买一样的礼物,从来不分远近。每到年底,父亲和祖母还都召集我们开一次家庭生活会,每个人汇报一年来的收获和来年的打算。这个传统让我们姐弟都从小就养成了善于学习,做事认真的好习惯,一辈子受益。值得骄傲的是,我叔家的三妹,在恢复高考后,成为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如今,我们十一个姐弟,无论是农民还是党员干部都是自律自强的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做着贡献。
父亲朴实无华,注重操守,对家乡情义深厚。在安平任县委常委期间,县委给父亲配备了公车,但他回家的时候多是骑自行车,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有时县委安排汽车送他回家,他就让车停在村边的一个厂子院内,自己再步行走到家,为人做事极其低调。对待乡亲们,父亲又是一个特别重感情,讲情义的人,安平县有个化肥厂是省市重点企业,南王庄则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都是邻近兄弟市县参观学习的榜样,武强县的不少干部都去参观学习,尤其是乡村干部比较多,他只要有时间就一定亲自陪同并到县界迎送。有时候,乡亲们为村集体买化肥找到他,只要不违反政策,他都千方百计帮助解决。
父亲淡泊名利,亲仁善邻,深受家乡乡亲们的爱戴和尊重。1983年,为响应党中央动员老干部提前退休的号召,父亲提前离休回到武强老家。我们族院有四十多户,由于过红白事标准不统一,起了争端,形成了分裂的态势,他便利用过年的机会,在大年初一,组织祭祖回来后,把本族院的80多名家庭骨干和长辈们约集到一起,讲历史,讲团结,谈未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最终统一了标准,建立了制度,解开了大家的疙瘩。在他的倡导下,全村在1987年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从此全村婚丧事一律简办,一直坚持至今,深得乡亲们的称赞。他还自荐担任了村小学校外辅导员,自编教材,每周给孩子们上一节思想辅导课,村小学连续3年被县里评为“十佳学校”。1990年,父亲又发起并带头集资搞旧校搬迁,村民们说,要是俊岭管账,俺们就集资,别人管账俺不集。结果我父亲亲自管账,群众踊跃集资。学校完成搬迁后,他把账目一分不漏地公布上墙,乡亲们非常满意。1992年,他又到县、乡联系,争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村里建起党员活动室兼老年人俱乐部,把自己搜集整理的本村革命史、老党员事迹图文并茂地搞成专栏,长期展出,活动室既是文化娱乐场所,又是宣传教育的阵地。1992、1993年,他连续荣获县“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被县委老干部局评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1993年,被省有关部门评为“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不知不觉27年过去了。想起父亲的面容,仿佛近在眼前,但却远出天边。无尽的思念,无以传表,只能轻轻地回望,默默地怀念。父亲的一生信仰坚定、朴实无华、善于学习、重情重义、为人忠厚、踏实认真,为我们子女和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始终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徐沛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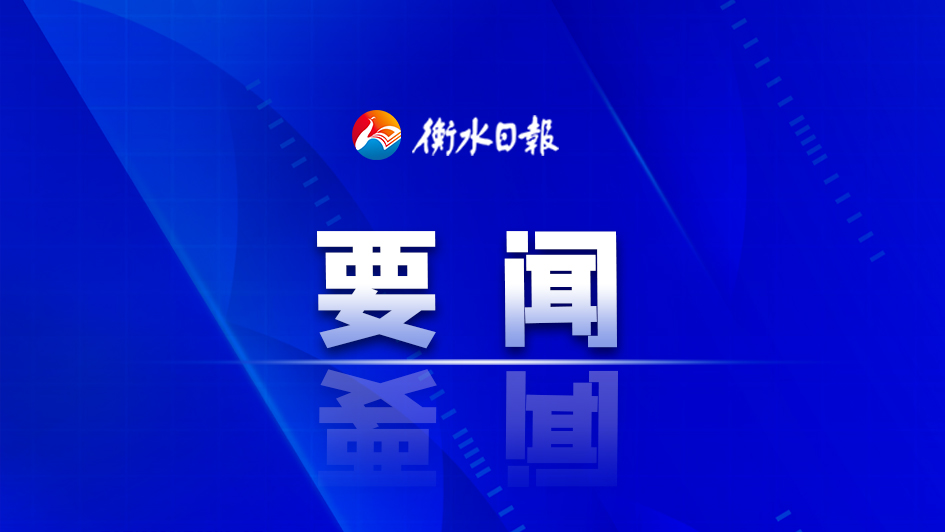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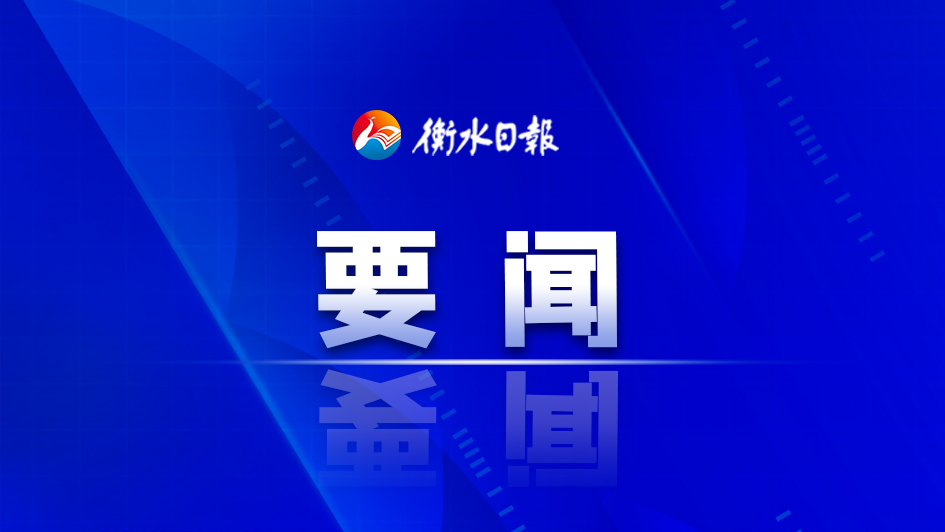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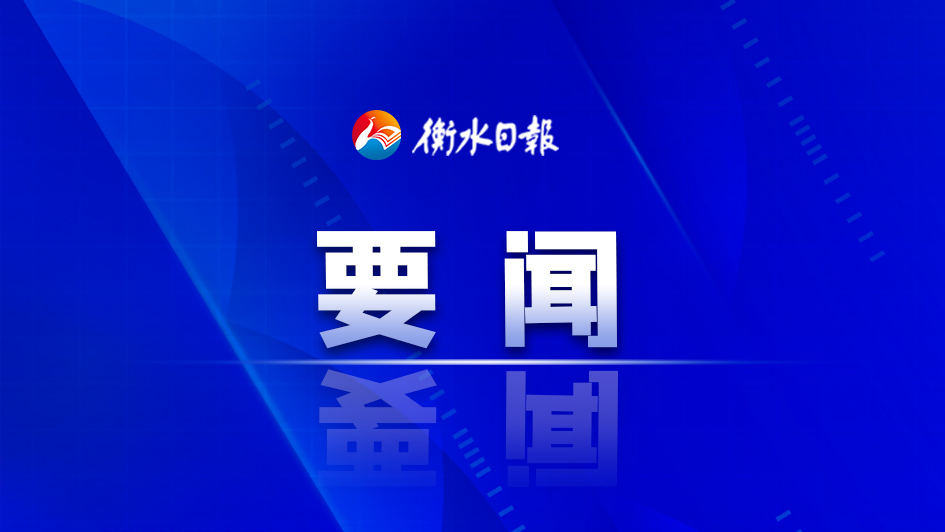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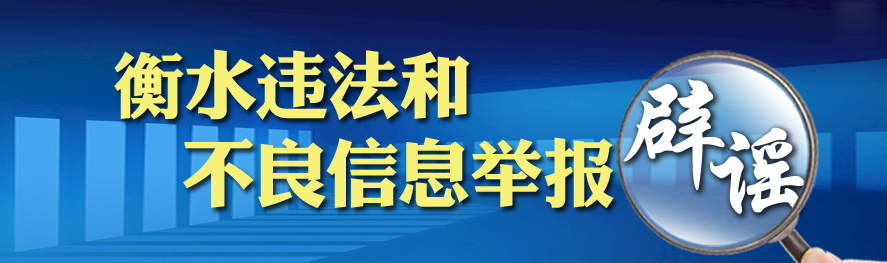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