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武先生的大名,是从安平县文联主席王彦博口中听到的,话题是谈其带几十名作家学者瞻仰孙犁故里的情形。
据说那天恰逢阴雨,乡路泥泞难行,但大家都争先恐后在村头下车,抱着朝圣般的心情踏进这个人杰地灵的村庄。刘先生作为带队人,大步走在前头,打着手势给人们讲解,所以虽撑着雨伞,仍旧淋湿了衣服和头发。当时孙犁故居尚未落成,但那次“朝圣之旅”给这些“犁迷”“荷粉”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听到这些情况,我眼前浮现出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壮年形象。及至去年看到他过世的信息和简历(2022年12月31日去世,享寿87岁),才知那次安平之行时,他已是古稀之龄了。
刘宗武不仅长期担任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还主持编选了《耕堂劫后十种》等孙犁著作和研究文集十几种之多。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十一卷本《孙犁全集》的出版说明中,还强调注明:“孙犁之子孙晓达先生对编辑方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刘宗武先生、段华先生在资料的收集和编订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就在那年,我和一位文友写了十几篇孙犁在饶阳土改和创作的系列文章,编成一本《孙犁在饶阳》的书稿,急于找几个专家把关求教,于是就自然想到刘宗武先生。但对这样全国闻名的专家,我们以前毫无渊源,不但未谋一面,甚至未通一信,所以寄去书稿自是抱着尝试的心态。令人惊喜的是,他对这本粗糙的打印稿本十分重视,还热情写来一封近四千字长信,坦诚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他首先肯定了我们的努力,鼓励说:“我们素不相识,是对孙老的敬仰、对孙犁作品的喜爱,把我们连在一起了。”“你们对孙犁在饶阳的日子——这恐怕是他一生最困难、早先最受冲击的一段日子,收集到许多宝贵的资料,特别是他的思想情绪,他的工作情况,都做了很全面、很深入、很有说服力的描述,这对研究孙犁一生是很有用处的。”然后又循循善诱提出自已的看法,要求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事实”,“语言要掌握分寸”“要避免篇章段落的重复”“不一定把小说人物对号入座”等等。
接到信后我们非常感动,反复阅读后深受启示,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尽力修改润色。这本小书因为是挖掘孙犁大师一段独特经历,受到很多作家和学者的肯定和赞扬。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题了书名,《文论报》主编封秋昌作序推介。给刘宗武先生寄书后,他马上回信说:“你们学习研究孙犁的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我作为曾与孙犁过往二十余年、又在天津市孙犁研究会工作十余年的人,对你们所做的一切,感到特别高兴和欢迎。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还在信中说:“我把你们的书给孙晓达看了,他同意我的意见,即对孙犁的事要做到真实可信,仔细又仔细,慎之又慎。”并说“这本书我建议你们寄给孙犁的子女孙晓达、孙晓平、孙晓玲及天津日报文艺部……”
原来我们对孙犁子女的情况不甚清楚,可能因为他的介绍,使孙晓达对这本《孙犁在饶阳》留下一点印象。后来参加一次安平县纪念孙犁大师的活动,有幸相遇孙晓达同志,他不但吃饭时与我碰了杯,还赠送一本自己签名的《孙犁纪念文集》。而这部厚厚的文集,主编正是刘宗武和段华。
长期以来,我曾几次萌动拜访刘宗武的念头,但拖延多年却未能成行。想来主要是因了自已的惰性,更与平时怕见名人的怯懦有关。我年轻时因在天津的《文艺》双月刊发过短篇小说,有次赴津出差就带着作品鼓劲想去拜访孙犁,但打听到地址后又突然消失了勇气,所以至今引以为憾。特别是看到大师曾给与我紧挨页码发稿的江西作者通信时,更是懊悔莫及。后来结识《孙犁年谱》的作者段华,他听了这件事笑着说:“你那时要给孙犁写信,先生也会回信的。”可惜,我虽终生崇拜孙犁大师,却无晤面聆教的机会了。
现在年至老境,自己又想拜访结识曾与孙犁密切交往的专家学者,这是一个业余文学作者近乎痴狂的天真,更是为了稍稍弥补一下心底的遗憾。最近与段华谈到已逝的刘宗武先生,段华沉痛地说:“他本来微信说春季天暖来京聚聚,没想到头一天给我微信,第二天就突然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心里的悲痛,你是可以想象到的。我失去了一个可以倾谈孙犁先生的真正挚友,几次想写他都没写,因为写起来心里会更疼更疼。”
得知我有两封刘宗武的长信后,段华先生非常看重此事,嘱我把文本发他存留,并恳切表示“今后编辑孙犁先生有关书籍时使用”。于是我迅速打印发给段华。这也算对刘宗武先生的缅怀和纪念吧。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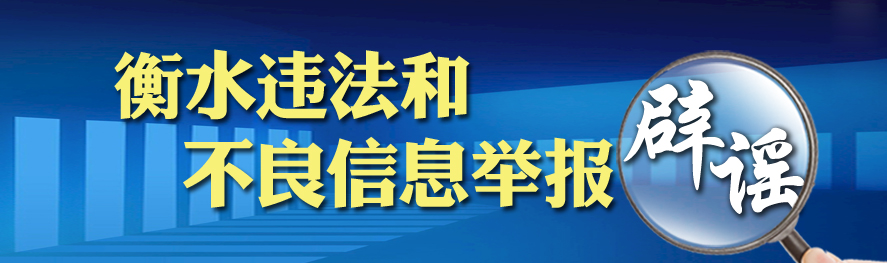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