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的西南角原是一片隙地,我搬来的前几年一直荒着。房价忽高忽低,开发商好像是无暇打理。后来市里整顿宝云街,临时在那里开辟了一个农贸市场,可由于商户们纷纷观望,入驻率不高,北半截空出了一大片场地。最近因为“创城”的需要,城管部门加大了市容巡查力度,便常有近郊的菜农骑着三轮车过来,零零星星地摆出几样自家菜畦里种的时令小菜,时间不长,相继招来了不少附近小区跳广场舞的大妈。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便是这个小小的自由市场最为热闹的时段。我时常出门打乒乓球,为抄近道(人都有走捷径的天然属性),喜欢从那里穿行而过。
开春之后,菜摊上先是出现了荠菜、面条菜和苜蓿苗。随着大地一天天回暖,蔬菜的品种日渐繁多起来。我最抵挡不过小葱的诱惑,水灵灵的一小捆儿,只需要两块钱。为了卖相好看,菜农们常把小葱择得干干净净,浅白的根,翠绿的叶,看一眼都招人欢喜。回想小时候,家家生活捉襟见肘,没有什么给小孩子解馋的蔬果,春天刚刚长齐的小葱甜而不辣,已是难得的好口味了。我对小葱有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执着的嗜爱,母亲从菜园里新割回家,我便迫不及待地抹掉根上的泥土,一绺一绺塞进嘴里大嚼特嚼,母亲看得瞠目结舌,给我取下一个“葱阎王”的绰号。那个年代里,新鲜的小葱、韭菜,自家也舍不得吃,常常要走村串巷去卖。我们小孩子会一路跟着卖菜人,贪婪地吮吸着菜根割口里溢出来的香气。卖菜人生意不好,也会心烦意乱地驱赶我们。我们一个个狗仗人势,破口大唱:小葱韭菜,人吃狗卖。也许是我们的恶作剧引来了看热闹的乡亲,一唱一和却成了最好的招牌,卖菜人的生意反而好了起来。过去村庄里的人们大多性情敦厚,就在这样不和谐的演唱中做成了和谐的买卖。他们甚至都没人站出来责怪我们,他们知道,日子穷苦,小孩子们也可怜呢。
我挑了一把小葱,转眼又看见相邻的菜摊上码着十来棵粉嫩鲜艳的小水萝卜,每一根水萝卜的红梗绿叶上还带着晶莹的水珠。想到汪曾祺先生作画,没有颜料还可用牙膏代替。三笔两笔,纸上便有了活灵活现的水仙、大蒜和荸荠,水萝卜也曾做过他的主角,便满心喜悦地买了回来。清水一洗,水萝卜的红粉之色愈加诱人,便试着按母亲的做法调制几个平原上流行的下饭小菜。萝卜梗去叶,切成末刀小段,拌细盐,加少许鸡精,滴几滴小磨香油,腌制一个时辰,晚餐就小米粥,可称极品;去掉的萝卜叶,盛在玻璃盏中,配另一玻璃小碗,碗中倒两小勺黄豆酱,萝卜叶蘸酱,清热解毒,若配有新出锅的白面馒头,口味绝佳;水萝卜竖剖,先切条,再切小丁装盘,均匀洒少许绵白糖,唇红齿白,如美人歌唱。佐白干三两,须小盅慢酌,咂一口春酿,嚼几粒萝卜丁,白干醇柔清冽,小菜甜脆爽口,不失为一世可遇而不可求的春饮。
无独有偶,水上勉在一本食记中也曾写到过萝卜。他认为,把一根萝卜的各个部位都能加以利用,细细理出,做成美味的食物。这就是修行,是精进。他讲到的萝卜产自轻井泽的山庄,与母亲的水萝卜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度。即便是佛国与俗世,惜物之心,也能不谋而合。
水上勉九岁出家。寺中住持与师父并不是每天为他传授佛学典籍,而是利用手边的食材来随心指导。有一次他洗菠菜,顺手扔掉了裹满泥巴、很难清理的菜根。住持走过来说:“不要把最好吃的部分扔掉啊。”由此我回想自己清洗菠菜,也常常因为贪图省事,把菜根整整齐齐剪下来,作垃圾扔掉了。这多么可惜!还有洗菜的水,其中有了大地的营养,我们可以浇到花盆里,不是更好么?
书中他还写道:食物除了有酸甜苦辣咸五味,还有第六味,叫作“余味”,就是吃了还想吃的味道。诗、书、画、音乐、写作,求得“余味”最难。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亦曾说:“人生和电影,都是以余味定输赢。”水上勉的外祖母,就是靠着吃罐子里腌制的山椒,活到了八十三岁。在轻井泽的厨房里,煮着以山椒做佐餐小菜的早饭时,他就会想起这个腿脚不便、卧病在床的山村老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深谙“余味”之美,它从祖先的舌尖之上,一辈辈滚动到我们的舌尖上来。食媒如同基因,承载着我们对祖先融入血液的庚续,绵延出我们对亲人无尽的思念。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一个古老的民族,总是与土地密不可分,与日升月落的简朴生活息息相关。
桃红李白,春天好颜色啊!就连楼角那几根铁棍一样生锈的枣树,也被春风搔得笑起来枝叶乱颤。可是没有了小葱和水萝卜,没有了“红嘴绿鹦哥”的菠菜,水上勉的素菜料理就少了一份惹人感动的食单,在汪老先生和我的评价表里,春色也要减几分吧。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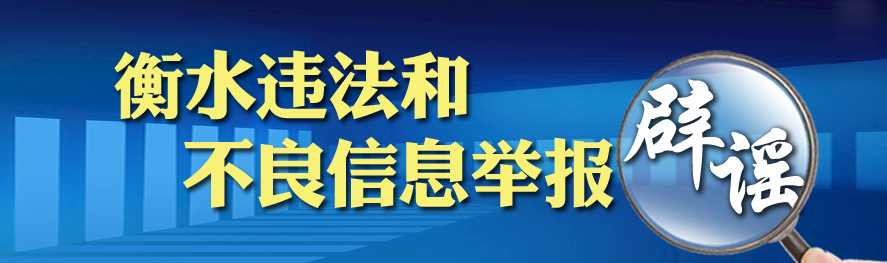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