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制作 李玲
汗与泪
“现在度日如年。并不是害怕,而是对时间的感觉出了问题,觉得这两天跟过了一两个月一样。其实是心里不踏实。惦记疫情,惦记那些病人,还不如在医院里忙着。”范立东有些困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
从第一例隔离观察者入院(1月24日凌晨)开始,第一梯队16名医护人员就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吃饭、休息既不规律,也不能保证时长。
“休息室就两张床,70CM宽的那种。大家就地隔离之后,没有办法休息,不得已就挤在一起睡,有时一张床挤2个人甚至3个人,每次能睡3到5个小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吃饭,赶上饭点的时候正在忙,就顾不上,经常推迟。”范立东说。
让所有人都觉得最难受的,是穿戴防护用具。“穿上防护服,那滋味简直无法形容,不到1小时人就会汗流浃背。脱下来,里面的衣服都是湿的。”李志军和不少同事近视,平时都戴眼镜,穿上防护服就更不方便。“护目镜外面还有防护面屏。待不了多一会儿,护目镜上就全是水汽,我们看东西都得斜着眼睛,从镜面缝隙去看。”
因为长时间佩戴N95口罩,大家脸颊、鼻梁皮肤被磨破,耳朵被勒得刀割一样疼。沉重的防护用具,让他们感到头昏、窒息。由于长时间不喝水,没过几天,不少人开始上火,眼睛红肿、声音嘶哑。

范立东记得,自己值班那天(1月28日),来病人最多。“一晚上来了11个。有经询问流行病学史要求过来隔离的,有因为接触过疑似病人自己要求隔离的,我们都不能拒收。那天晚上李主任(李志军)也在,12点左右我们就开始准备,干吧。先是说3个,放下电话10分钟又是3个,最后又来了4个,其中一个是半植物人状态的老爷子。”
“那天晚上确实是比较疲劳。本来是计划第二天让4楼的(肺三科)来协助我们,结果当天就紧急调了2名医生过来。那一夜,没有一个人睡过觉,一直干到天亮。”
薛军英说,所有医生的手机都不允许关机,必须24小时随叫随到。“那时主任(李志军)已经在科里值了好几天了,24小时在岗。这段时间事情很多,我们要随时向他请示,他和医院、专家组协调。”
1月25日(正月初一)晚上9点,李志军接到市里专家组通知,去衡水市人民医院接病人,“其实是两例,一对夫妇。”接回来之后,薛军英是主管大夫。“基本上是谁值班、谁接来的病人,谁就主管。如果病人太多管不过来,会分流一些。”
“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每人负责一个病人,医生一个班上24小时,第二天休整,护士每6小时倒班。病人一多,就做不到了。”李志军说。

护士长郭玉丹是河北医科大学高级护理专业的毕业生,已经在市三院工作了十多年。她从1月26日(正月初二)进了隔离区就再没出来,接电话、发微信语音,嗓子都是嘶哑的。“我们科护理人员一直处于轮流倒班状态,职责所在。”
执行医嘱治疗、标本收集传递、补充领用物品、各区域卫生消毒、为病人送水送饭……郭玉丹说,护士们工作繁琐劳累,还要克服很多心理障碍。照顾卧床行动不便的病人,要定时为他们翻身、处理排泄物。
“我们分工也不是那么严格,紧急的时候就一起上。帮一个病人翻身得三四个人……穿着防护服,行动特别不方便。”另一位护士长赵春燕说。
赵春燕发愁的问题,也是防护用品紧缺。“我们尽量延长在隔离区内的时间,从6小时到8小时,越来越久。”
总不喝水,上火越来越严重。护士韩海杰下眼睑通红、肿得老高,还在岗位上坚持。一天中午,护士高琦因为穿防护服时间过久、闷热窒息,刚摘下护具就开始呕吐。
护士刘旭盼说,因为防护用具影响视线,她们采血、输液,需要依靠经验去摸索操作,难度是平时的几倍。
护士侯雅芳没怎么说话,悄悄拭泪。她在惦记孩子。
郭玉丹忍不住感叹,这个年过得实在太漫长了。“都在盼着疫情赶紧过去,我们能早日回家团聚。愿身边的每个人都平安!”
偶尔停下来,第一梯队的成员们反倒不适应了。
“这两天就是聊天……实际上我们每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已经快把能聊的话题都聊完了。”范立东说,市里给协调的宾馆比医院环境条件要好,大家能按时作息、吃饭,但心里并不踏实。
“疫情之前,人们说一说歇班,一天一夜不去医院,心里会觉得不自在。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做派——交完班看一眼自己的病人、其他病人,同事在一起交流交流。该做的做完,能提前准备的提前准备。这样心安。”
现在,第一梯队休整的成员已经陆续重返岗位,再次投入到阻击疫情的战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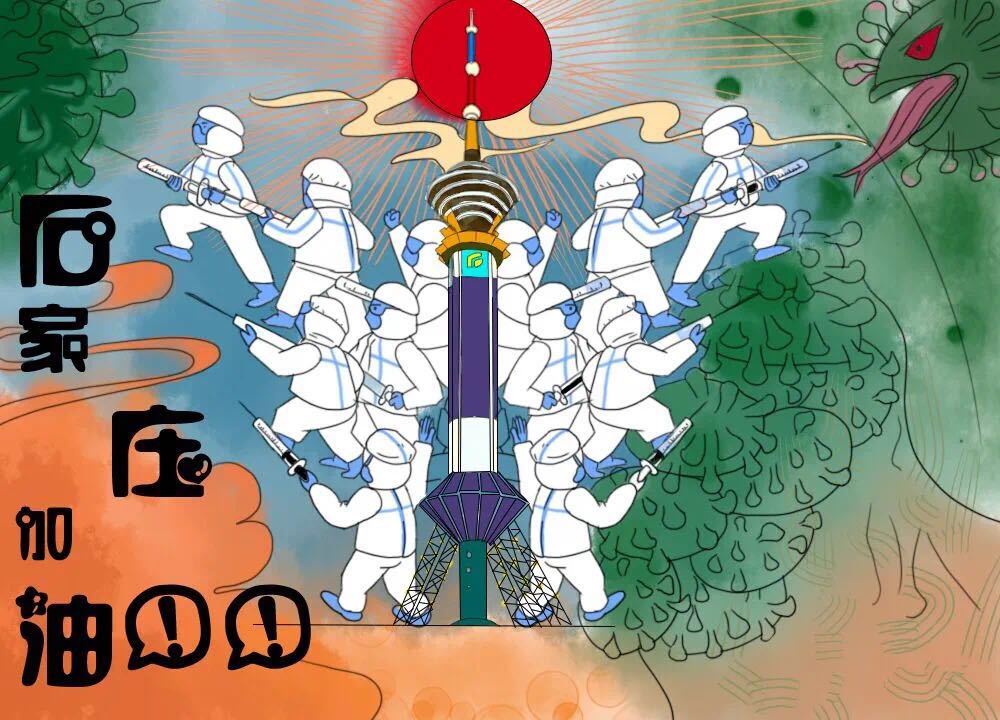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