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冀中平原,故城境内,运河西岸,大堤脚下,有一个绿柳环抱的村庄,那是我的故乡。村北几间土坯茅屋,那是父亲的老宅。老屋上空升起的缕缕炊烟,那是母亲描绘的画卷。几十年的沧桑岁月尘封了我许多记忆,唯独老宅上的炊烟却使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离家几十年,每当回家探望,看到房顶上飘荡着袅袅炊烟,闻到老宅内散发着秸秆烧焦的清香,心中不由地升起一种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童年的回忆。
往日的家乡,每当三餐前,家家户户屋顶上不断地升腾着缕缕炊烟。那炊烟交织在一起,随风飘荡,形成一片片青白交汇的云朵,盘旋在村庄的上空,显摆着小村的朝气,炫耀着故乡的生机。那炊烟里孕育着浓浓的乡情;那炊烟里承载着母亲的呼唤;那炊烟里充满着游子的思念。
母亲的炊烟,总是最先迎来黎明,最后送走黄昏。每当拂晓,东方刚刚泛起一丝鱼肚白,第一缕晨曦还没有挤进窗棂,母亲便早已穿衣起床,抱来秸柴,点燃灶火,接着便响起“咕哒、咕哒”的风箱声。这声音划破黎明前寂静的夜空,冲出小院,飞向左邻右舍,合奏于千家万户,形成浑厚雄壮的交响乐曲。踏着这优美的旋律和娴熟的节奏,灶堂内欢快的火苗随风跳跃、翩翩起舞。通红的灶火映红了母亲那勤劳的身影,调皮的炊烟不时地窜出灶口,亲吻一下母亲那沧桑的脸庞,然后便顺着烟囱飘向空中,盘旋在屋顶上,蜿蜒曲转,形似蛟龙,形成一幅美丽壮观的天然画卷。

清晨,炊烟是劳作的号角,它唤来黎明的曙光,拉开忙碌的序幕。每当家家户户屋顶上飘起炊烟时,胡同里便现出忙碌的身影,院子里也传来鸡狗的叫声,于是,整个村庄便沸腾起来。母亲撒米喂鸡,父亲拌料喂牛,孩子整理书包,家家都奏响劳作的序曲。饱腹之后,望着老屋上空飘散未尽的炊烟,大人走向田间,孩子奔向学堂。
中午,炊烟是小憩的港湾。每当午时,家家户户都飘来美味佳肴的香甜,这扑鼻的芳香伴随着缕缕炊烟散向空中,飘向远方。午餐是三餐之主,尽管当时家境贫寒,但勤劳的母亲都会尽量做出丰盛的饭菜,或全家享用,或接亲待客。丰盛的午餐、飘香的美味,不仅是填肚充饥、补充能量的源泉,而且是牵引游子思家的纽带,更是期盼游子归来的信念。
傍晚,炊烟是家庭的召唤。每当夜暮托起晚霞,缕缕炊烟裹卷着美味飘香冉冉升起时,田埂里劳作的父亲便卸下犁耙,牵着他的老牛收工回家;放学的孩子也望着屋顶上那缕缕炊烟踏门而来。然后,一家人或于厅堂之中,或在土炕之上,围桌而坐,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一边品尝着母亲粗粮细作的美餐,一边谈论着邻里的奇闻趣事,盘算着自家的美好生活。没有时间约束,没有他人催促,一直到很晚很晚……
就这样,一日三餐被这世世代代延续不断的炊烟熏蒸着,被这千年一律永恒不变的旋律催熟着……
母亲的炊烟像一位翩翩少女,那柔美的身条婀娜多姿,随风飘逸。在细雨绵绵时,她喷洒如雾;在雪花飘飘时,她挥散如花。她淡淡的身影弥漫在屋顶上空,那一派朦胧景象让整个村庄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和生机。炊烟渲染成的一幅幅图画,不知陶醉了多少诗人和画家,让人沉醉其中,不舍离去。
母亲的炊烟,写就了千年乡史,诉说着乡村往事。它是一条永恒的纽带,牵系着游子的衣襟;它是一盏指路的明灯,牵引着游子的脚步;它是一怀故乡的情缘,牵动着游子的魂梦。
母亲的炊烟养育了我,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母亲的炊烟永远飘荡在老宅上空,飘荡在我的脑海里,飘荡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上。
作者:王玉飞 编辑:王常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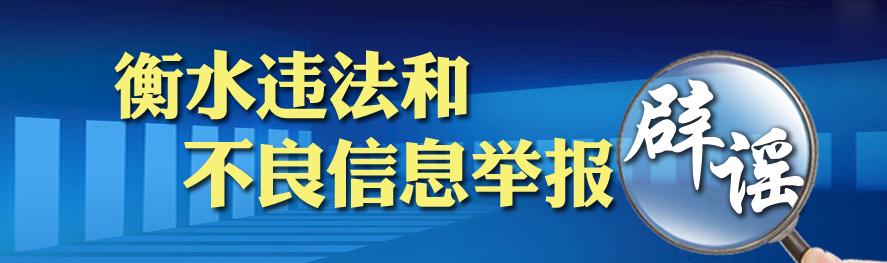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